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恩登布仪式当中一些主要象征符号的特性和语义结构,并且区分了这些象征符号所具有的意义的三个“层面”或“领域”。每种狩猎仪式本身就是恩登布文化中一个部分的概要,一个典型的构件就是那些临时立起的祭坛,它们为猎人祖灵而立。这些祖灵可能正使他活着的亲属遭受困扰,也可能已得到安抚,成为顺利猎杀动物的好运之源。祭坛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但会随具体仪式不同而与更多象征单位相连。......
2024-01-21
祭天仪式之“理论”[1]
钟鸣旦(比利时鲁汶大学)
在一篇题为《礼仪之争的若干简单议题:一个将来研究的计划》[2]的文章中,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提请研究者注意中国礼仪之争的仪式方面,对于比较欧、中仪式系统可能具有的意义。在文章的结论中,他认为:“晚明的儒教仪式观念值得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欧中关系史,同时也利于我们从总体上去了解礼仪”。[3]
本文便试图为这样一个大的研究计划做出微薄的贡献。为深化对相应的仪式文化的了解,它将比较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和欧洲的)礼拜仪式。讨论的重点是两种“祭天”仪式:中国的大祀和欧洲的天主教弥撒。之所以选择这两种仪式,原因在于17世纪中、欧的作者已经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传教士使用祭天这个关键词,来作为表达弥撒仪式中给天主献祭的专用名词。[4]结果,在中国信徒的辩护文字中,他们觉得不能不向其中国同胞这样解释:神父做日常弥撒时,并不想篡夺天子祭天的无上权力:“这两种仪式名同而实异”。[5]而且,下文我们将会发现,近世的作者也常常比较这两种仪式。
本文的讨论基于两个规定性文本。在简短描述资料之后,我们将分析这两种仪式的结构和内容,目的是处理与祭天有关的若干基本问题:这些文本是写给谁的?谁是主要的仪式司祭?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在两种仪式中,口传因素和书写因素各有什么地位?最后,它们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资料:这里用以讨论晚明大祀的主要资料是《大明集礼》(五十三卷)。[6]它首先于1370年由徐一夔奉旨编纂。之后,又在李时(1471—1539)的主持下进行了修订和扩充,于1530年,亦即嘉靖朝(1522—1566)大礼仪的中间,由皇帝作序、刊行。[7]它记载了各种官方仪式的则例,包括截至嘉靖初年的朝会和接见外国朝贡使者的规定,内含描述仪式器具和仪式布局的插图。和之后成书的《大清通礼》,进行比较颇具价值。这是一本关于如何举行朝廷仪式的手册。乾隆元年,即1736年,乾隆皇帝下令编纂此书,1756年由他的仪式指定者编纂完成。Ange1a Zito对大祀的研究就是基于这本仪式手册的。[8]
在欧洲传统中与之相应的文本是《弥撒经典》(1670年在北京刊印),[9]它是由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根据Missale Romanum(1570)翻译而成的。这部著作包含对弥撒仪式的描述及对在弥撒中所使用文本的介绍(圣经文本和祈祷文)。1685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曾努力争取罗马教廷认可这个中译本,但没有获准。不过,不管是拉丁文本还是中文本,都清晰地描述了弥撒仪式(Ritus Servandus)。[10]
《大明集礼》的编纂者沿用古老的分类法,将仪式分为五类: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和凶礼。[11]祭天(也称祀天)是吉礼部分的第一种仪式,共二卷。卷一首先进行总体介绍,接着描述了这一仪式的重要内容(牺牲、祭服、仪式用具等)。[12]卷二首先提供祭天场所圜丘的示意图和仪式布局,然后是这一祭祀本身的不同步骤的清单,接着是对仪式器具的描述。
《弥撒经典》在结构上有细微的不同。第一册开篇描述了西洋历(西历年月;De Anno et ejus partibus)。接着是弥撒的“公例”,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弥撒、在仪式中朗读的文字、法衣和法器(弥撒公例;Rubricae genera1es Missalis)。这部分最令我们感兴趣的地方,是对仪式本身的描述。紧跟其后的是弥撒仪节和祈祷文(弥撒礼节;Ritus servandus)。不过,这部著作最重要的部分(第二到五册)的内容,是用于礼拜中朗诵的祈祷文和圣经选段。它们是根据礼仪周年和主要节日进行编排的(时弥撒本经;Proprium de tempore;(共)圣人本弥撒;Missae Votivae)。弥撒的次序和纲领(弥撒次序;Ordo Missae;弥撒纲领;Canon Missae)被置于第三册的开头。
根据书面的规定性资料来研究这些仪式,只能得出有限的结论,因为这些文本未必对应于实际表演的仪式。但是,这些文本是研究16、17世纪这些仪式如何运作的主要资料。况且当时方兴未艾的印刷业,不仅影响到礼仪书本身的生产,而且影响到仪式本身。《弥撒经典》便是很明显然的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的教会中心都有各自的弥撒书(布拉加、科隆、里昂、米兰、美因茨、托莱多等)。同样,各宗教团体的主要修道院(Cluny 1080,Cîteaux 1134)也拥有整个团体自身使用的弥撒书。这些弥撒书经常是在神父的任命仪式举行的那一刻抄写的,随后神父将根据这个仪式(手册)念弥撒。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的决定和出版社提供的机缘给这个系统带来了变化。1570年,罗马一地的礼拜书,成为特利腾大公会议举行两百年前以来未按本地自身习惯进行仪式的所有教堂的弥撒书。换句话说,这种印刷的弥撒书使得全世界——包括中国——在时间上同步(亦即同时)举行仪式成为可能。
严格说来,刊刻大祀的必要性比较小,因为少数手抄本已足以满足帝王和官员举行仪式的需要,理由是,表演这一仪式者原则上别无他人。不过,中国仪式手册的目标在于达成某种历时性(亦即历史时间)的统一。尤其当它们成为仪式专家的参考书时:“仪式符号的宗旨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创造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和谐。”[13]对于像《大明集礼》这样一个在仪式改革的过程中出版(再版)的文本而言,这个规定性的特征显而易见。
仪式与时间:历史与方法
《大明集礼》卷一包括三十小节,描述了祭天大祀的各个不同方面:祭坛、祭服、音乐、祭器、牺牲等。每小节的特点是,各自均严格按照历史和编年的结构进行编排。编纂者对每一朝代每个方面的实践都做了历史的回顾。总叙便是一个不错的例证。
总叙:
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
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所从来尚矣。
周官大司乐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经》曰:“周公郊祀后禝以配天。”所以重报本反始之义。而其礼则贵诚而尚质,见于遗经者可考也。
秦人燔书灭学,仍西戎之俗,立四畤以祠白、青、黄、赤四帝。
汉高帝(前206—前195)因之,又增北畤,兼祠黑帝。至于武帝(前140—前87),有雍五畤之祠。又有渭阳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至元帝(前48—前33)时,王莽谄事元后,傅会“昊天有成命”之诗【《诗》271】[14],合祭天地,同牢而食,其亵尤甚。
光武(25—57)祀太一,遵元始(1—5)之制,而先王之礼,堕废尽矣。
魏晋以来,郊丘之说互有不同。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宝、苍帝威灵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纪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谓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龙见而雩,总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也。宗王肃(195—256)者则以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行之。
而至唐为尤详。武德(618—626)、贞观(627—649)间,用六天之义,永徽(650—655)中从长孙无忌等议,废郑玄议,从王肃说。乾封(666—667)中,复从郑玄议焉。
宋太祖(960—976)乾德(963—967)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丰(1078—1085)中,罢合祭。哲宗绍圣(1094—1097)、徽宗政和(1111—1117)间,或分或合。高宗(1127—1162)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
元初,用其国俗拜天于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1302),建坛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1305),始立南郊,专祀昊天上帝。泰定(1324—1328)中又合祭,然皆不亲郊。文宗至顺(1330—1332)以后,亲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
国朝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仁祖淳皇帝配,其从祀则唯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皇帝每岁亲祠。参酌成周、唐、宋之典,以适其中。盖不牵惑于郑玄谶纬之说,可谓明且至矣。[15]
最后一段反映的是嘉靖朝爆发的大礼仪之争期间进行的一次重要讨论的结果,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天地祭祀的分合问题。洪武帝(1368—1398)最初在劝说之下,采纳了分祀的形式;但至1377年,他对大祀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确立了合祀天地的做法。嘉靖帝决定光大其皇室旁系在统治家族和朝廷中兴中的地位,1530年,在这一决定的激发下,他亲自对大祀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一个措施就是重新确立分祀天地的祭礼。[16]
这些礼仪的历史被置于《大明集礼》对仪式的描述之前,这反映了仪式的一个本质因素:它们与历史,与对历史的诠释相关。在中国的朝廷礼仪中,经典文本的历史和诠释,乃是皇帝和士大夫之间就官方宗教一再进行角逐的场所。仪式手册是由那些谙熟礼仪事务的儒家官员编纂的。他们通常比皇帝更熟悉经典,因而成为正统的仪式传统的维护者和传承者。[17]
通过和(缺乏历史视角的)《弥撒经典》的比较,中国仪式传统的这一特殊性将更为显著。在欧洲,改革所关注的仪式,并非仅由一人表演,而是由许多神父在不同地方进行表演。虽然在特利腾大公会议引发的改革中,新礼仪手册的编纂者依据的是先例,但其重点并非要让神父与历史保持一致,而是要达成共时的一致性。在当时欧洲的情境下,就某个可以完全按照一己见解表演仪式的个体(比如,教皇)而言,并不存在专门纠正其行为的仪式专家。相反,当时存在的是一个由主教组成的(经常是松散的)等级结构,这些主教借助更加统一的结构,避免许多神父在仪式实践中的越礼行为。
然而,《弥撒经典》第一章展现了仪式时间的另一个方面:它以描述西历开头。在中、欧仪式中,历法和仪式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祭天(在冬至日举行)和弥撒庆典都属于“节序仪式”的类型,亦即伴随光照、气象、农事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季节变化,根据历法、周期性地以可预料的方式进行表演的仪式。[18]众所周知,在中国,对协调仪式和天文周期非常重要的年历,是由钦天监提供的。[19]在中世纪欧洲,礼仪历法的作用也非同一般。在一个没有大众传媒的年代,乡村的仪式生活是根据自然季节和天主教节日来安排的。某些节日的日期是固定的(所谓固定的节日,如每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但也存在不固定的节日(像复活节,其日期每年都在变)。因此,除了阅读礼仪文本的能力外,计算复活节的时间(computum pascale)也是神父群体的一项重要能力。只有那些精通数学的人,才能算出准确的日期。正是这个历法的应用及随之而来的仪式实践,解释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化的程度。“广义的天主教文化的真正尺度必须是,以天主教礼仪年对时间、空间和仪式节日进行实质性的定义和控制的程度的深浅”。[20]
《弥撒经典》中文版历法部分包括下列几个部分:
1.西历年月(4a)
2.闰年(4a)
3.瞻礼说(4b)
4.移动瞻礼[共九个:圣灰星期三、棕枝主日、圣星期四(圣餐规定)、圣星期五(受难日)、复活节(耶稣复活)、耶稣升天日、圣灵降临节、三一节(4b)]
5.周年不移动瞻礼表(例如,一月一日:耶稣圣名;12月25日:圣诞节)(4b—6a)
6、四季大斋(6a)
7、历年移动瞻礼表[自丙辰(1676)至乙卯(1735)](7a—11a)
8、历年推瞻礼日法(11b)
9、周年各等瞻礼日(标出各自的等级:加倍,加半,或憶文,12a—21a)
天主教历法[21]在《弥撒经典》中的出现,让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耶稣会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例如,他们对天文和历法科学的痴迷——与他们的仪式和礼拜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历法及其相应系统的特点是,“作为从仪式的角度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产物,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塑造,大到人类生活的本质具备了历法的维度”。[22]犹太—天主教星期中的安息日或礼拜日便是再清楚不过的表现。因此,通过将一种新的历法引入中国,传教士不只是纠正或协调了中立地分隔时间的某些技术层面,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挑战了仪式生活的基础本身:将自然的时间转换成文化的(cultural)、因而是礼拜的(cu1tua1)的时间。
仪式脚本
在历史和历法部分之后,《大明集礼》和《弥撒经典》给出了仪式本身的脚本。首先摘引这两部著作的两个部分。[23]
《大明集礼》第十节,“初献”一段:
赞礼唱:“行初献礼”。太常卿奏:行初献礼。请[皇帝]诣爵洗位。导驾官同太常卿导引皇帝[24]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执爵官以爵进。
皇帝受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爵官。执爵官又以爵进。
皇帝受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请诣酒尊所。导驾官同太常卿导引
皇帝升坛,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执爵官以爵进。
皇帝执爵。司尊者举幂,酌泛齐。
皇帝以爵授执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请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导驾官同太常卿导引
皇帝至昊天上帝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司香官捧香,跪进于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
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执爵官捧爵,跪进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乐舞止。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读祝官取祝版于神右,跪,读讫。乐舞作。太常卿奏:俯伏,兴,平身。稍后,鞠躬,拜,兴,拜,兴,平身。
皇帝俯伏,兴,平身。稍后,鞠躬,拜,兴,拜,兴,平身。乐舞止。……[25]
《弥撒经典》第八节,“纲领至祝圣”一段:
一、序文念毕如前,铎德立台中,向台略起手,目仰天主,即恭敬俯下,复合掌按台上,深鞠躬,起,纲,先领默念“故尔至宽仁”云云,[26]见《弥撒次序》。合掌享降福亲台中,后起,胸前合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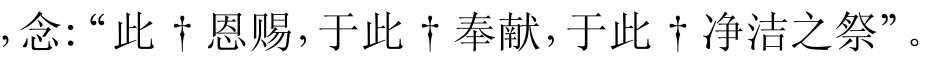 画十右手字。圣饼、圣爵上后,胸前开手,继念:“先奉献于尔”云云。
画十右手字。圣饼、圣爵上后,胸前开手,继念:“先奉献于尔”云云。
二、至念“偕尔仆。念“吾主教某”,称一方他主教下,不念别上司之名。……[27]
五、若另有将祝圣饼匣,铎德未取圣饼,以右手取匣子盖,前经念毕,置肱台上,俯首,分明谨慎,而微声圣饼上发祝声之语。若将祝圣多饼,须并发其语众圣饼上,以大指、食指持圣饼,念“盖此即吾体也”。念毕,铎德以食指、大指持圣饼台上,跪拜圣体,起,举扬,目仰圣体,恭敬示众共拜。举扬圣爵亦如是。即时以右手置圣帕上,复归原所,以后非取圣体,大指与食指合,不分开,至领圣体后,盥手才开。[28]
这两种文本的性质并不相同。仪式手册通常不只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定性的。在《大明集礼》中,这两种因素转变为叙事性的。好像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一位叙述,者告知一位在场的人(盲人)。这种叙事角度最为清楚的表现,是将即将发生的事情(官员奏请皇帝)和实际的行动(皇帝的表演)重复一遍。在《弥撒经典》中,描述性—规定性的维度表现为一整套的规则。这些规则试图预计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例如,在念教皇的名字时,如果教皇过世了,该如何处理。
司祭和仪式文本
《大明集礼》和《弥撒经典》的不同性质,引出了关于仪式文本和司祭之间关系的问题。从文本本身来看,我们不太清楚《大明集礼》是为谁编纂的。它不像是为皇帝而编的规定文本,倒更像是为谙熟朝廷礼仪的官员或是从来都不会参加这些仪式、却又对之感兴趣的官员而编纂的传授知识的文本。光从这些描述本身判断,便知它并不是为主要的司祭编纂的。上述段落中(但也见于通篇文本)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皇帝的角色完全是被动的。若无明确的指示命令,他便不采取主动或是行动。他的所有动作,都是由导驾官、太常卿、赞礼、执事官(如执爵官)引导的。而且,所有关键的动作(鞠躬、俯伏、上香、祭酒)都不必求教于仪式专家,因为所有中国人从小就在家礼中演练了这些肢体动作。换句话说,皇帝本身肯定不需要仪式手册。而真正需要知道仪式细节和次序的是那些仪式助手。照这样说来,他们才是真正的司祭。那种认为皇帝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说法看来颇值得怀疑。尽管官方仪式文本认为皇帝在仪式上有亲自主持大祀的义务,明初的皇帝只是坚持祭天,也许还坚持祭祀皇室祖先;大约从1540年开始,连祭天也大为堕废。[29]Taylor说得很正确:“这些祭祀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如果它们真的要按规矩做,那么,这个事实便让这些祭祀变成皇帝善意的抵押品。”[30]正因为如此,通过历史文本和专职的仪式官员来保存这些仪式,便变得很重要。
在转入讨论《弥撒经典》之前,为彰显儒教和道教各自传统仪式的特色,不妨先对儒教和道教的礼仪书进行一番简单的比较。对于这个问题,劳格文(J.Lagerwey)的看法是:“每个单独的[道教仪式]确实有相应的礼仪书,而且事实上人们对之尊崇有加,更不用说为避开世俗的眼光,满怀戒心地将之妥善收藏了。然而,与仪式——步骤(démarche)——本身相比,礼仪书甚至不配称为脚本:要制作这样一个脚本,必须至少校对四种抄本——仪式抄本、简谱、榜文及与口述传统一致的‘秘诀’。除非表演仪式的道士已完全掌握了脚本——也就是说,他掌握了演奏各种乐器、唱歌、舞蹈、朗诵等技能,否则它根本就无从存在。”[31]这与朝廷的祭天仪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皇帝并没有扮演乐师、歌手、舞蹈家或是朗诵者之类的不同角色。他做的姿势——俯伏或奠酒——与其他仪式并无二致。知识借以在师徒、父子之间传递的口传传统,在这里并不需要。而且,在这个脚本中,似乎并没有变异或变通的空间或必要。一切都准确按照仪式手册来进行。在历史上,这种变通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但是它们与其说是表演仪式的皇帝发明、创造的结果,不如说是编写仪式脚本的仪式专家争论和诠释的结果。
比较之下,弥撒仪式手册的地位大致在大祀和道教仪式之间。在天主教传统中,神父是主要的司祭,《弥撒经典》是为他,而不是为历史学家或仪式助手编纂的。神父兴许得到了助手的帮助,但这些助手引导神父的方式,与中国的仪式助手引导皇帝的方式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这些助手可有可无。因此,担任司祭的神父必须大致掌握仪式的姿势和言辞。这在《弥撒经典》中就有体现。上文提到的段落的内容集中于姿态,因为经文文字的完整文本需要另辟专章介绍(这些经文最好能默记,参见册三,《弥撒纲领》)。而且,姿势规定得非常详细(如在持圣体时,手指如何放置)。这些是必须通过拜师才能学会的。与大祀相比,神父可以说将皇帝和读祝官的角色合而为一。与道教仪式相比,天主教神父也歌唱或朗诵,但他不像道士那样演奏乐器或舞蹈。礼拜仪式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神父的创造性和个人能力(如他是否擅长唱歌)。但从《弥撒经典》的规章看,其目的在于限制过多的差异。除了礼仪文本之外,由其他神父组成的团体整体也维持着仪式的延续性。
口传与书写
欧、中仪式中司祭被指派的不同角色,也体现在口传和书写因素在各自仪式传统中的不同地位上。口传传统优先于书写传统,是欧洲仪式的重要特征,而在中国仪式中,书写传统优先于口传传统。[32]书写文字的重要性在道教仪式中便有明显的反映,这个特征在大祀中也可以观察到。例如,与昊天的交流不仅需要口头的言说,而且需要书写的文字。在祭祀中呈献的祝文,是在仪式前两天就由内阁大学士写好,接着在仪式前一天由皇帝审阅,在仪式过程中,再由读祝官大声地朗读的。这表明,书写文字仍然需要通过口头传递,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由皇帝亲自念的。最后,在仪式结束时,祝版要被焚化。[33]这种祝文的沟通方式,指出了大祀仪式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在整个仪式中,皇帝没有说一句话。口头表达的言辞包括:乐生唱的歌、赞礼者宣告不同仪式步骤的唱礼声、太常卿的奏请、或者读祝官所读祝文。皇帝则保持沉默。
这与欧洲的弥撒仪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为大部分言辞都是由神父说的:祈祷、经文、讲道、献祭词。这些言辞有着不同的功能。有些是祈祷,亦即人类对天主(上帝)讲的话。礼拜仪式一个重要部分是《圣经》选段,这是体现神启的固定文本。大众朗诵这个文本的行为,事实上是在重新激活天主言辞的启示(亦即公诸于众)。祝圣饼仪式中的以言行事式的言语,是由此刻替代基督的一个人类成员言说的。这些话只能由正式任命的神父来言说。这些言辞将司祭转变为一种媒介,一个天主的工具。这个维度在道教仪式中也有体现,但在儒教的朝廷仪式中几乎完全不存在。[34]
进而言之,可以说两种礼拜仪式反映的是各自对天和天主的观念。在中国,被动、沉默的天的观念,反映在皇帝扮演被动、沉默的角色的礼仪上;在欧洲,积极、言说的天主(逻各斯logos)的观念,反映在行动和言辞占据核心位置的礼仪上。
隐秘的宇宙仪式
在描述仪式风格的种类时,Catherine Be11将一种特殊仪式风格的特征归纳为“宇宙秩序的建构”。她认为:“其焦点在于在仪式中重建人、神领域之间的完美和谐。这种仪式实践的形态,一般出现于中央专制君主维系庞大但不完全同质的政体的社会或政治体系中。由中央统治阶级倡导的世界观,尽管与更具地方色彩的态度并不一致,却预想了一个唯一的、巨大的宇宙秩序。所有的事物、人和神灵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35]在Be11的眼中,传统中国的国家祭祀便是这种世界观的一个典型例证。
不同作者的看法都与这种对大祀的诠释相同。他们都强调皇帝表演祭礼的这一宇宙观维度。在一篇讨论中国宗教特征的通论著作中,周克勤(Christian Jochim)将下列这些角色归结到皇帝身上:
通过表演旨在协调人类社会与宇宙关系的仪式,中国的皇帝将自己树立为道德典范而非暴君,一如北极星,无需使用强权,便可君临天下。他也借此摆明自己贵为天子——统治宇宙之力量的合法代表。但作为天子,他是代表昊天的责任代理人。惟有成为公正且谋取万民福祉的统治者,他才获得统治人类的权力。他自身并不是神,而是具备导管功能的人类,君临天下的权力通过这个导管,最终延伸至充任中国官僚机构官员的儒家士大夫的手中。[36]
Romeyn Taylor在讨论明朝官方宗教的研究中,同样强调宇宙秩序的建构如何成为祭祀的核心:
祭礼表演乃是官方宗教的核心。祭礼可以被理解为宇宙的盛会,它是借助统治者的权威在整个朝廷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和神灵组成的大共同体的周期性的更新。它成功与否,是以对和谐与福祉的体验的深浅来衡量的。这种体
验的深浅,端赖于准备阶段的斋戒和心神集中程度,言辞、姿势、颜色、音乐和舞蹈的和谐,筵席的芳香、燃香和醇酒的混合。[37]
官方宗教礼拜仪式的设计,旨在创造一个小宇宙,用以表达天、地、人的宇宙的三位一体性,宇宙过程的周期性以及宇宙元素的等级秩序的建构。只有当这些条件满足之后,仪式的参与者才有可能“感神”。[38]
最后,在讨论大祀的著作中,Ange1a Zito也将皇帝视为借助祭祀行动与宇宙相通的人。(www.chuimin.cn)
贯穿全年、重复举行的大祀,在空间和时间上(在三个方面)将皇帝和他的大臣组合起来:对天地的祭祀表明,皇帝是连结两者的纽带。在中国人思想中耳熟能详的天、地、人的宇宙三合一结构中,皇帝反复声称自身作为连结宇宙的地位。[39]
所有这些诠释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大祀是表演性的,也就是说,皇帝举行仪式的即时效应,便是宇宙秩序的建构。在此我想指出,与其说大祀的表演性力量来自礼仪的行动或是皇帝的行为,倒不如说来自所缺席和隐秘的,来自皇帝的被动性和围绕仪式的种种禁忌。
首先,平民是缺席的。当然,也有公众的参加,但这几乎完全是由朝廷内核的成员组成的:朝廷官员和其他朝廷成员,高级官员和专司仪式的官员。但是,平民不得参加这些仪式。因此,天主教的弥撒在大多数情况下预设了一(大)群平民的参与,相比之下,中国祭礼的力量与其说依赖于这些官员的参与和观看,不如说依赖于平民——正如在几乎所有其他内廷的活动那样——并不参与和观看这一事实。正是由于仪式活动是隐秘的,平民才会相信皇帝能够通过祭祀带来宇宙秩序的建构。
其次,任何言辞或演说也有类似缺席的情形。在整个仪式中,皇帝并非言语的诠释者:他既不用读,也不用说“好话”。在天主教传统中,礼拜中的启示性言辞是其本质特征,相比之下,朝廷祭祀的大部分言辞并非启示性的。正统首先不是通过言说,而是通过文本注疏者承传的文本传播的。
再者,皇帝自身扮演的是消极的角色。他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为,而是始终保持沉默,很像北极星,稳而不动,而所有其他星辰都围着它转。皇帝不仅在仪式中相当被动,甚至还会发生皇帝本身缺席的情形。虽然他本该亲自去表演这个仪式,但他的确可以委派代表去完成祭祀。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司空见惯。这是个富有意义的悖论。祭天大祀绝对是皇帝的特权,但委派代理人却显然不会影响“宇宙秩序的建构”。在道教或天主教仪式中,这样一种替代根本就不可能。
也许,最为重要的维度就是仪式的禁忌。皇帝是否参加仪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其他人——不管官员还是平民——都不得擅自举行这个仪式。对此,C.Be11对中国朝廷仪式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实际上,建立在宇宙秩序建构之上的官方仪式系统,能够也愿意为那些处于神明系统低端的地方神腾出空间。同时,对于那些预设更具‘平和与感召力’的世界观的仪式实践,官方系统始终试图加以控制,偶尔将之铲除。对于涉及灵媒和地域神或鬼的地方崇拜行为,一种传统的批评意见是,它们违背了与天交流的合法等级。这种违背规范的接触,不仅威胁到宇宙系统的秩序,而且牵涉到皇帝特权的预设,是一种僭越的行为(lèse majesté)。”[40]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天主教仪式在中国的冲突的问题。中国官员把罗马天主教弥撒当作对其现存体系的威胁,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众所周知,在这个仪式中,神父直接与最高的天进行交流,平民和官员以相同的方式参与这个仪式,共享同一块献祭过的圣饼,这是对等级权威的“宇宙秩序建构”的严重挑战。然而,通过比较《大明集礼》和《弥撒经典》中的祭天仪式,这个特殊仪式的某些其他维度被揭示出来。从《大明集礼》历史部分的叙述来看,它的宗旨是达到一人表演的仪式的历时性统一;而《弥撒经典》想要实现的是由多人表演的仪式的共时性统一,这是一个由礼拜历法部分执行的维度。在大祀中,皇帝扮演的是消极而隐秘的角色:他不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他的姿势是无师自通的,与天的交流表现为书面和非个人的、口头的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维持了宇宙的秩序。在欧洲的弥撒中,神父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出现:他采取主动的行为,他的仪式姿势需由师傅传授,与天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个人、口头的方式。这样,他的仪式反映的是逻各斯在世界中的角色。
《大明集礼》所载大祀的步骤
1.斋戒
2.告天下神袛
3.告庙
4.省牲
5.陈设
6.銮驾出宫
7.迎神
8.奠玉帛
9.进熟
10.初献
11.亚献
12.终献
13.分献(高官表演)
14.饮福受胙
15.徹豆
16.送神
17.望燎
《弥撒经典》所载的弥撒的步骤
1.将祭预备仪则(接受弥撒书,准备圣杯,穿上礼拜法衣)
2.赴台
3.弥撒始与悔罪经
4.进台主矜怜天主受享
5.祝文
6.经书陛经等至献经
7.献经等至纲领
8.纲领至祝圣
9.祝圣后纲领至天主经
10.天主经等至领圣体
11.领圣体与领圣体后祝文
12.弥撒毕降福与圣若翰万日略经
13.遗于已亡者弥撒
(陈贵明译,刘永华校)
【注释】
[1]戴卡琳(Carine Defoort)、杜鼎克(Ad Dudink)、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孙尚杨和Valeer Neckebrouck对本文初稿提出了批评,作者谨致谢意。此外,感谢Fonds Voor 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Vlaanderen和Onderzoeksraad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为本研究提供的资助。本文的英文版:“The‘Theory' of Rituals Related to Heaven”,in Noël Golvers&Sara Lievens,eds.,A Life1ong Dedication to the China Mission,Leuven: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2007,PP.521—543。
K.Schipper,“Some Naïve Questions about the Rites Controversy:A Project for Future Research”,in Federico Masini(ed.),Western Humanistic Cu1ture Presented to China by Jesuit Missionaries(ⅩⅦ—ⅩⅧcenturie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1d in Rome,October 25—27,1993,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96,PP.293—308.
[2]戴卡琳(Carine Defoort)、杜鼎克(Ad Dudink)、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孙尚杨和Va1eer Neckebrouck对本文初稿提出了批评,作者谨致谢意。此外,感谢Fonds Voor 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Vlaanderen和Onderzoeksraad Katho1ieke Universiteit Leuven为本研究提供的资助。本文的英文版:“The‘Theory' of Ritua1s Related to Heaven”,in Noë1 Golvers&Sara Lievens,eds.,A Life1ong Dedication to the China Mission,Leuven: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2007,PP.521—543。
K.Schipper,“Some Naïve Questions about the Rites Controversy:A Project for Future Research”,in Federico Masini(ed.),Western Humanistic Culture Presented to China by Jesuit Missionaries(ⅩⅦ—ⅩⅧcenturie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1d in Rome,October 25—27,1993,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96,PP.293—308.
[3]Schipper,前揭文,页308。
[4]比如,参见对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弥撒的论文:艾儒略的《弥撒祭义》(1629)。
[5]参见杨廷筠《代疑篇》(1621)第13章(《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页565以下);另一种表达方式“瞻礼”避免了这个问题。
[6]哈佛—燕京图书馆微缩胶卷,复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86,第650册。普林斯顿东亚图书馆善本书TB287/1623和802。比较Wolfgang Franke(傅吾康),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页189—190。《太常续考》八卷,17世纪40年代(复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86,第59册),可以补充这部著作的信息。太常寺是负责举行主要祭祀典礼表演的机构《,太常续考》便是讨论太常寺的论著。书中包括太常寺在整个明代的则例和活动和《大明集礼》的续篇。对其他资料的讨论,参见Romeyn Taylor,“Chapter 13:Official Religion in the Ming,”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8: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2,ed.D.Twitchett&F.W.Mo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840—892,特别是“Bibliographica1 Notes”,PP.1001—1003.对明代国家祭天的描述,也参见Joseph S.C.Lam,State Sacrifices and Music in Ming China:Orthodoxy,Creativity and Expressiveness,New York:SUNY,1998,页23以下。
[7]对大礼议的讨论,参看Taylor,oP.cit.,PP.858—860;James Geiss,“The Chia-ching Reign,1522—1566”,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I,ed.D.Twitchett&F.W.Mo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40—450;Rudolf Herzer,Zum Staatskult der Ming-Dynastie:Die Reform der Staatsopfer in der Ära Chia-ching(1522—1566),Wiesbaden:Harrassowitz,1995.
[8]Angela Zito,Of Body&Brush: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Zito好像并不知道卷一到卷十六已经被译成法文:Ch.De Har1ez,La religion et les cérémonies impéria1es de 1a Chine moderne,d’aPrès le cérémonial et les décrets officie1s,Brussels,1893.
[9]梵蒂冈图书馆藏,Borgia Cinese 352。必须注意的是,本书的另一名字叫《昭事经典》,昭事一词(“虔诚的服侍[上帝]”)被用作弥撒的别名。这个词也被用作设有上帝圣坛的昭事庙的庙名,此庙由顺治帝建于紫禁城,可能是在汤若望的影响下建立的。顺治帝只在这座庙中献祭过一次(顺治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即1658年10月17日)。康熙帝在登基之后,就废除了祭祀上帝的仪式。参见朱庆征:《顺治朝上帝坛:昭事殿始末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页74—81。
[10]研究弥撒历史和意义的最优秀的成果是:Joseph Jungmann,The Mass Of The Roman Rite: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Missarum Sollemnia),trans.F.Brunner,London:Burns&Oates,1961(4th ed.).
[11]Zito前揭书,页150—151,注释3:五礼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书经》。《周礼·大宗伯》首次列举、解释了整个系列。
[12]《大清通礼》的版本不包括这个卷一的信息。
[13]De Harlez,前揭书,页10。
[14]译者注:《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15]《大明集礼》卷一,页1a—3a;对类似的描述(《实录》的概述)的讨论,参见Taylor,前揭文,页852—853,854—855。
[16]Taylor,前揭文,页851。《大明集礼》的序言是在皇帝下令大臣进行朝议之后,于1530年阴历六月写成的。在这次朝议中,192位官员支持分祭的做法;206位官员反对,而198位不表态(Geiss,前揭文,页458)。
[17]比较Schipper,前揭文,页304。
[18]对此类仪式的讨论,参见Catherine Be11,Ritual: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页102—108。
[19]对晚明朝廷祭祀及相应日期的时间表的讨论,参见Taylor,前揭文,页843—845。
[20]John Van Engen,“The Christian Middle Ages as an Historiographical Prob1e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3(1986),页543。
[21]对天主教历法的讨论,参见Noёle M.Denis-Bou1et,The Christian Calendar,London:Burns&Oates,1960。
[22]Be11,前揭书,页108。
[23]参见附录的不同章节内容清单。
[24]这个格式是中文原本的格式“,皇帝”要换行顶格写。
[25]《大明集礼》卷二,页19a—20b。
[26]这段文字选自《弥撒次序》,在此引述了下面的拉丁文段落:“Te igitur clementissime etc.”;“Uti accepta habeas et benedicas”; dona,haec
dona,haec munera,haec sancta
munera,haec sancta sacrificia”;“In Primis quae tibi offerimus,etc.”;“una cum famulo tuo Papa nostro N.”;“et Antistite nostro N.”;“Hoc est enim Corpus meum”(比较《弥撒经典》)。
sacrificia”;“In Primis quae tibi offerimus,etc.”;“una cum famulo tuo Papa nostro N.”;“et Antistite nostro N.”;“Hoc est enim Corpus meum”(比较《弥撒经典》)。
[27]《弥撒经典》,f.44a。
[28]《弥撒经典》,f.45a。
[29]Taylor,前揭文,页842;对清代委托祭祀做法的讨论,参见Evelyn S.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页211以下。
[30]Taylor,前揭文,页857。这在正德年间已变得极为明显。正德皇帝在其统治后期,成功地将仪式减少到滑稽的境地。
[31]John Lagerwey,“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n”,in Gert Naundorf(ed.),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niger zum 65.Geburstag,Würzburg:Königshausen&Neumann,1985,P.305.
[32]比较Lagerwey,前揭文。
[33]《大清通礼》,ff.页3a—3b,5b—7a。比较Zito,页159,164,194。
[34]比较Lagerwey,前揭文,页312以下。
[35]Bell,前揭书,页187。
[36]Christian Jochim,Chinese Religion,Englewood C1iffs:Prentice-Hall,1986,P.148.
[37]Taylor,前揭文,页847。
[38]Taylor,前揭文,页848。
[39]Zito,前揭书,页2—3。
[40]Be11,前揭书,页187—188。
有关潘富恩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的文章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恩登布仪式当中一些主要象征符号的特性和语义结构,并且区分了这些象征符号所具有的意义的三个“层面”或“领域”。每种狩猎仪式本身就是恩登布文化中一个部分的概要,一个典型的构件就是那些临时立起的祭坛,它们为猎人祖灵而立。这些祖灵可能正使他活着的亲属遭受困扰,也可能已得到安抚,成为顺利猎杀动物的好运之源。祭坛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但会随具体仪式不同而与更多象征单位相连。......
2024-01-21

朱熹对“慎独”的误读及其在经学诠释中的意义梁涛慎独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内容人们一般理解为“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或“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然而据新出土的简帛材料,以上理解乃是后人的一种曲解,并不符合慎独的原意。本文拟对朱熹的慎独思想作出分析,并探讨其在朱熹经学诠释中的特殊意义。这里的“独”与《五行》一样,都是在“舍体”的意义上使用的。所以更应在平时慎其独,诚其意。......
2024-04-04

根据可诉性的相关概念可知,受教育权的可诉性是指当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当事人能够向法院等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诉权对于“可以享有的权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7]因此,诉权能够在诉讼过程中要求国家或有关单位对公民的“可以享有的权利”进行保障。......
2023-07-22

破产理论的研究源于1903年瑞典精算师Filip Lundberg的博士论文,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但Lundberg最初的研究缺乏严密的数学基础。目前,破产理论已成为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研究保险公司所面临风险的一门学科,关于这一领域的具体介绍可以参阅出版的一些专著,如Embrechts等。在财产保险业中,重尾分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个体索赔额的标准模型。......
2023-07-06

注意义务是一种法律义务,行为人违反了这种义务,发生危害结果的,就构成过失犯罪,所以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来认识注意义务的性质问题。因此,注意义务实际上为过失犯罪和行为人之间架起了一个桥梁,也框定了行为人在刑法上进行选择的行为模式。刑法以注意义务为核心来界定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并进而确定过失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2023-08-15

厄舍尔称其为一种“先验论”的观点。吉尔菲兰对发明的英雄观持否定态度,他明确指出“人们普遍误解了发明的本质”;“我们依然处于远古地质时代,对事物的产生认为是大洪水造成的灾变论的、而不是进化的观点,重大的发明被认为是某些伟人制造的”[11]。这一时期发明社会学理论表现出明显的否定英雄发明家的倾向。吉尔菲兰借用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来反对发明的英雄理论:个体发明者、发明的组合累积模式和发明的系统化、组织化。......
2023-11-27

虽然,埃及和中亚国家有长期的文化交流,但是,埃及人们偏爱动物,而亚述人和波斯偏爱植物,这表明了文化和思想的差异性。所以,人们在物品中采用植物这些自然界的形象。再现的过程可能就是植物的人性化过程。前面的观察和推理并不否认亚述和波斯坐具缺乏能力、财富和侵略企图的象征性。首先,自然的美与有用性联系在一起,而植物是自然的象征,也是生命力的象征。......
2023-06-22

《社会记录》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晚间10点30分首播的新闻栏目。另外,《1860新闻眼》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电视界引入“公共新闻”理念的标杆栏目。(一)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电视实践1988年总统大选之后,美国社会充斥着对于政治及新闻界的批评声,投票率创下新低。可以说正是这种公共新闻意识的真正渗透,使得《社会记录》在新闻选材、处理视角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民生新闻或社会新闻的独特性。从题材角度来看,《社会记录》的......
2023-11-23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