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章崔溥《漂海录》校勘记引言1. 6种版本的对校2.对校结果的分析3.对中国文献的校勘小结引言在朝鲜时代,崔溥《漂海录》在壬辰倭乱之前和之后,各出版3次。崔溥《漂海录》有6种版本之多,非常有必要通过对校,对文字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调查。1964年,在金灿顺第一次节译了崔溥《漂海录》。笔者先对崔溥《漂海录》的6种版本,进行了对校,想在决定研究所需底本时,留下确实的根据。......
2023-11-30
3章 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 (漂海录)》
(漂海录)》
引言
1.从《唐土行程记》到《通俗漂海录》
2.《 漂海录》的谚解和手抄时期
漂海录》的谚解和手抄时期
3.《通俗漂海录》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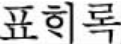 漂海录)》的错误
漂海录)》的错误
4.《通俗漂海录》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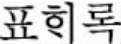 (漂海录)》之比较
(漂海录)》之比较
小结
引 言
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地知道,崔溥《漂海录》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的。仅知道在壬辰俊乱前刊行的3种版本,在韩国都没有留下来全本,也许是战乱时,混入到倭军掠夺的朝鲜典籍中,从而流传到日本。崔溥《漂海录》被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清田君锦(1721—1785)[1]翻译为日本语,明和四年(英祖四十五年,1769)以《唐土行程记》作为书名,在京都出版刊行,在26年之后,又改名为《通俗漂海录》。
当朝鲜只能是一部分属于“识字阶层”的人,才能阅读以汉文写下的《漂海录》时,日本的庶民百姓们从18世纪后期开始,就可以阅读用日本语翻译的《漂海录》。在朝鲜,从19世纪后期开始,虽然也有谚解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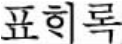 (漂海录)》的手抄本,但是难以找到这本书广泛流传的痕迹。由于《通俗漂海录》和《
(漂海录)》的手抄本,但是难以找到这本书广泛流传的痕迹。由于《通俗漂海录》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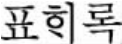 (漂海录)》是把崔溥《漂海录》原文压缩后进行的翻译,所以难以和原书保持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翻译上的错误仍然非常明显。在这两个译本中,《
(漂海录)》是把崔溥《漂海录》原文压缩后进行的翻译,所以难以和原书保持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翻译上的错误仍然非常明显。在这两个译本中,《 (漂海录)》,仅是存在着单纯的误译和过分的压缩而已,但是《通俗漂海录》不仅错字和误译百出,还有故意对文字进行的润色,它暴露出译者在论评中,对朝鲜极其露骨的歧视性观点是确实存在的。
(漂海录)》,仅是存在着单纯的误译和过分的压缩而已,但是《通俗漂海录》不仅错字和误译百出,还有故意对文字进行的润色,它暴露出译者在论评中,对朝鲜极其露骨的歧视性观点是确实存在的。
日本的《通俗漂海录》,相当于朝鲜的所谓“坊刻本”。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在18世纪的朝鲜,为什么韩文《漂海录》的坊刻本没能出版问世?直到19世纪的朝鲜,除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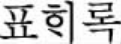 (漂海录)》手抄本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版本问世?这可以成为比较18—19世纪朝鲜和日本两国的出版印刷文化的重要线索。
(漂海录)》手抄本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版本问世?这可以成为比较18—19世纪朝鲜和日本两国的出版印刷文化的重要线索。
1.从《唐土行程记》到《通俗漂海录》
清田君锦将崔溥《漂海录》,译为日语的《唐土行程记》,并在江户时代的明和四年(英祖四十五年,1769)在京都的书店皇都书林出版刊行。对于《唐土行程记》的译者清田君锦的人品、著作、史观,牧田谛亮已经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评述。[2]我们分析清田君锦的译本,首先,清田君锦在翻译时,到底是使用了《漂海录》的哪个版本作为底本?从《唐土行程记》出版的年份来看,朝鲜时代的《漂海录》6种版本中,除了《华山文库本》以外,其他之前的5种版本,都有成为底本的可能性。[3]但是《唐土行程记》以“旧跋”的题目,收录了柳希春的“隆庆三年跋文”,在结尾处,又添加了校正者之一的倔荣吉撰写的几句话。
清先生所翻译漂海录原本,即朝鲜刊本,无有序跋。近阅高氏所藏写本,有崔希春跋二首,[4]因取其一,详言斯书,之由者附之卷末云。[5]
但是,在笔者调查的《漂海录》6种版本中,没有序言或跋文的版本,只有初刊本《东洋文库本》。因此,清田君锦在翻译《唐土行程记》时,使用的底本可以断定是东洋文库本。牧田谛亮虽然认为“君锦依靠的朝鲜刊本,最后隆庆三年序2页偶然缺失来看,其刊本可以推测为与阳明文库保存的朝鲜刊本是同一版本。[6]这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存在东洋文库本,所以这仅是牧田谛亮的臆测而已。
《唐土行程记》的底本是东洋文库本的一个例证,我们来看一看崔溥一行在杭州短暂停留的2月8日的记录。某某曾经问过崔溥,是否知道当年给事中张宁作为使臣出访朝鲜时,留下的诗文《皇华集》。崔溥当时就马上回答道,以“汉江”为题的诗文最佳,并且即刻吟出了几句。但是这首诗,准确的标题是“登汉江楼”,所以阳明文库本以后的所有版本,不顾每行17字变为18字,插入“楼”。[7]但是《唐土行程记》中仍为“汉江ニ题スル诗”,从仍旧把诗的题目介绍为“登汉江”来看,可以认为是把东洋文库本作为底本来翻译。[8]
《唐土行程记》是节选压缩崔溥《漂海录》后翻译的,所以不是全译本。在译文中,处处有清田君锦以“考曰”开始的简短思考,这是可以体现18世纪日本知识分子思考倾向的绝好资料。在译文序言的“考”中,对崔溥《漂海录》和朝鲜历史进行了简略的说明,尤其是把书名由《漂海录》改为《唐土行程记》的原因,进行了如下的说明。
这本书的原本是朝鲜的崔溥所写,叫《漂海录》。虽然如此,但是因为是记录了唐土(中国)里程的事情,所以改称现在的名称。[9]
对于清田君锦翻译本书的原因,牧田谛亮谈到“我认为这是由于对中国本土,沿着大运河从宁波至北京两岸的街道风光,或中国的事务有了大量的兴趣,这也告诉了我们,当时日本文人对中国的文化的倾倒程度。[10]但是更为重要的,我们还要在后面论述,本书的翻译工作并不是因为译者本人的想法开始的,是否是因为商业性出版社的劝说,才开始翻译的呢?在18世纪通过海洋和中国进行的民间贸易非常活跃的日本,出版社判断在大洋上的漂流故事、中国江南和大运河周边的情报,可以吸引大众的兴趣,这才是决定出版翻译本的原因。
皇都书林出版《唐土行程记》26年之后,在宽政七年(正祖十九年,1795),这本书又通过东都书林、浪华书林、皇都书林的合作,以《通俗漂海录》改名后,再次刊行。[11]把书名由《唐土行程记》改为《通俗漂海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出版社判断更改后的书名,更具有大众阅读兴趣。此时,因为清田君锦已经去世10年,书名的变更与译者显然没有什么关系,仅是因为出版社想要改变标题而已。
牧田谛亮把京都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通俗漂海录》和《唐土行程记》进行比较后,就其结果进行了如下的论述。
京大本《通俗漂海录》的第4册,卷尾中有伊藤圣训的跋,平安书林文锦堂藏板目录2页,在各书的末尾没有罗列校正者的1页,版心是没有“通俗”2字的《漂海录》。[12]
但是根据笔者调查京都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通俗漂海录》的结果,《通俗漂海录》中有伊藤圣训的跋文。不仅如此,除京都大学图书馆保存有《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之外,在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也收藏了《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13]我们对这4本书的目录进行严谨的比较,其结果如下。
续表
从上表来看,虽然刊记内容一样,但是可以知道目录的排列顺序各自不同。从根本上讲,《通俗漂海录》原样使用了《唐土行程记》的版本,仅换了标题和卷首题,版心题面则从“行程记”换为“漂海录”的事实,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对《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的内容进行讨论时,也是把底本确定之后再进行探讨。笔者认为更应该重视比《唐土行程记》晚26年出版的《通俗漂海录》。两种不同馆藏地的《通俗漂海录》中,应以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标准的,这本书的标题和卷首题为“通俗漂海录”,版心题只有“漂海录”而已。如果查看《通俗漂海录》的内容的话,文字排列顺序如下。
题言:平安 江村绶
通俗漂海录卷之序:柚木太玄
通俗漂海录目录图:41小题
附言六条:清绚
插图:9幅
通俗漂海录卷之一
通俗漂海录卷之二
通俗漂海录卷之三
通俗漂海录卷之四
旧跋:柳希春隆庆三年跋文附堀荣吉识文
跋:伊藤圣训
刊记:宽政七年乙卯六月
在这本书中,有清田君锦的二哥江村北海,即江村绶的题言和江村北海的弟子袖木太玄的序文。我们再次查看通俗漂海录目录的话,有《漂海录》原书中没有的41个小标题,从而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内容。但是小标题仅罗列在目录中,在正文中则没有。“附言六条”以6个条目进行整理,作为清田君锦对自身的翻译进行“提示”的文字。
我们认为在原书中是没有插图的,但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引起读者的兴趣,出版社增添了9幅插图。分别是海鳅图、西湖图、扬子江图、黄河图、无支祈图、孔林图、阙里形胜、北京、点苍山。但是,正如我们在下表中可以确认的是,目录中罗列的插图的标题,和9幅插图有不一致的地方。即使“黄河运河”可以充当“黄河图”来看,“泰山”和“阙里形胜”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而在目录中出现的“南海西海”、“吴三桂”、“渤海图”根本没有插图,而“点苍山”仅有插图,在目录中没有。[14]
和原书《漂海录》分为三卷相比,《通俗漂海录》分为四册。我们把译本的41个小标题和内容,与原书制表对比如下。
在结尾部分,收录了柳希春的“隆庆三年跋文”,其后有堀荣吉的短小识文,并有清田君锦的侄子伊藤圣训的跋文,同时还有“宽政七年乙卯六月”这样的刊记。
本书的书名,在日本的牧田谛亮以《唐土行程记》指称以来,韩国学者们也无意中沿袭了《唐土行程记》的称呼,[15]以后希望学术界以《通俗漂海录》来统一称呼,似乎更为恰当。其理由有如下三条。第一,《唐土行程记》虽然是清田君锦以日语刊行时第一次使用的书名,但是26年后改为《通俗漂海录》,以后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日本沿用了这个书名。第二,《唐土行程记》是“唐土(中国)行程的记录”的意思,这并没能很好地体现本书的书名。第三,从根本上讲,因为是崔溥《漂海录》的译书,所以应该突出“漂流的记录”的意思,为了让大众更通俗地理解,我认为使用《通俗漂海录》是更合适的书名。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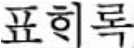 (漂海录)》的谚解和手抄时间
(漂海录)》的谚解和手抄时间
虽然比18世纪日本的《通俗漂海录》稍晚,但是朝鲜也在19世纪出现了用韩文翻译的谚解本《 (漂海录)》。现在这谚解本《
(漂海录)》。现在这谚解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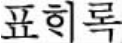 (漂海录)》,被收藏在国立中央图书馆胜溪文库。由于这一时期没有出现《
(漂海录)》,被收藏在国立中央图书馆胜溪文库。由于这一时期没有出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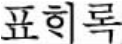 (漂海录)》的刊印本,因此可以判断这一手抄本可能是用韩文翻译的《
(漂海录)》的刊印本,因此可以判断这一手抄本可能是用韩文翻译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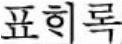 (漂海录)》的唯一版本。
(漂海录)》的唯一版本。
这一谚解本分为《 (漂海录)》、《
(漂海录)》、《 (漂海录第二)》、《
(漂海录第二)》、《 (漂海录三)》共三卷。分卷方式比较生硬。译文好坏本身先不评论,就连基本的空格都没有(韩国的基本文法),甚至在日期都已经变化的情况下,都没改换段落。这与利用日历中的纸张等细节一起,成为特别爱惜纸张的最好证明。因此分册时,更多地是根据文章分量多少,分为三卷。
(漂海录三)》共三卷。分卷方式比较生硬。译文好坏本身先不评论,就连基本的空格都没有(韩国的基本文法),甚至在日期都已经变化的情况下,都没改换段落。这与利用日历中的纸张等细节一起,成为特别爱惜纸张的最好证明。因此分册时,更多地是根据文章分量多少,分为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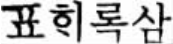 (漂海录三)》记录停留在3月15日为止,我们实在是无法知道剩余的部分是缺失还是遗失,还是手抄本在中间中断。崔溥赴任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得到父丧消息的日期是弘治十九年(1488)正月30日,到越过鸭绿江回国的6月4日为止,以“日录”形式写成的整体记录,而在此中断部分连一半都不到。因此《
(漂海录三)》记录停留在3月15日为止,我们实在是无法知道剩余的部分是缺失还是遗失,还是手抄本在中间中断。崔溥赴任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得到父丧消息的日期是弘治十九年(1488)正月30日,到越过鸭绿江回国的6月4日为止,以“日录”形式写成的整体记录,而在此中断部分连一半都不到。因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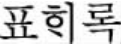 (漂海录)》在分量上,仅有原书的一半左右。
(漂海录)》在分量上,仅有原书的一半左右。
在《 (漂海录)三》的封面中用毛笔字写下了“止庵公朴夫人遗墨”。看来朴夫人可能不是单纯的传抄者,更可能是译者。如果那样的话,《
(漂海录)三》的封面中用毛笔字写下了“止庵公朴夫人遗墨”。看来朴夫人可能不是单纯的传抄者,更可能是译者。如果那样的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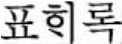 (漂海录)》不是其他手抄本,是朴夫人亲自翻译的抄译本。
(漂海录)》不是其他手抄本,是朴夫人亲自翻译的抄译本。
尹致富根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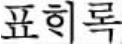 (漂海录)》的封面写的“癸酉历书”文字,把手抄时间的最早年代限定为燕山君八年(1513,癸酉年),最晚年代限定为高宗十年(1873,癸酉年),同时根据日历中纸上写的日期,小心地推定手抄时间为高宗十年(1873)左右。[16]但是笔者在尹致富上述的推定基础上,更进一步把《
(漂海录)》的封面写的“癸酉历书”文字,把手抄时间的最早年代限定为燕山君八年(1513,癸酉年),最晚年代限定为高宗十年(1873,癸酉年),同时根据日历中纸上写的日期,小心地推定手抄时间为高宗十年(1873)左右。[16]但是笔者在尹致富上述的推定基础上,更进一步把《 (漂海录)》的谚解时间推定为高宗十年(1873)以后,并打算在谚解本的内容中找到可以证明的蛛丝马迹。
(漂海录)》的谚解时间推定为高宗十年(1873)以后,并打算在谚解本的内容中找到可以证明的蛛丝马迹。
崔溥一行在2月4日左右到达绍兴,受到了总督备俊暑都指挥佥事黄宗为首的一班官员的审问。黄宗质曰:“初,以汝辈为抄寇之倭船,欲擒而诛之。若为朝鲜之人,当细书以其国沿革、都邑、山川、人物……以史书校之,以验其实。”对此,在崔溥记述朝鲜的沿革和都邑中,有如下内容:“今,吾国改名朝鲜,迁都汉阳,已逾百年。”对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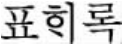 (漂海录)》的译者作了如下翻译:“今天,我们成为朝鲜,把汉城作为都邑,将要五百年了。”
(漂海录)》的译者作了如下翻译:“今天,我们成为朝鲜,把汉城作为都邑,将要五百年了。”
在此把朝鲜以易姓革命代替高丽,迁都汉阳之后的时间,从“百年”改为“五百年”的事实,可以知道将这些内容修改后翻译的原因是,从朝鲜建国开始到崔溥那时为96年,即接近百年,但是对完成谚解的人或阅读谚解本的读者而言,“百年”是不正确的,对他们而言是“五百年”。因此调查朝鲜建国之后接近五百年的“癸酉年”的话,即为高宗十年(1873)。如果准确地说,应是离五百年还有十九年的481年,即“将要达到五百年”。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放过之处,即手抄本的封皮使用了癸酉历书这一点。作为历书,一定是把失去价值的历书,重新利用为手抄本的封皮。由此看来,谚解本《 (漂海录)》的手抄时间只能是高宗十年(1873)之后。
(漂海录)》的手抄时间只能是高宗十年(1873)之后。
3.《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的谬误
《通俗漂海录》和《 (漂海录)》都不是全译本,如同其他节译一样,其内容和《漂海录》不可能完全一致。首先,进行了日文翻译的清田君锦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其误译的部分,也有理解错误的部分,同时还有误译和意译的分界线比较模糊,不能明明白白地认定为误译的部分。另一方面,和清田君锦一样,有译者进行润色的地方,或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补充了新的句子。另外,非常露骨地贬低崔溥或朝鲜的内容也并不少见。在日译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型。
(漂海录)》都不是全译本,如同其他节译一样,其内容和《漂海录》不可能完全一致。首先,进行了日文翻译的清田君锦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其误译的部分,也有理解错误的部分,同时还有误译和意译的分界线比较模糊,不能明明白白地认定为误译的部分。另一方面,和清田君锦一样,有译者进行润色的地方,或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补充了新的句子。另外,非常露骨地贬低崔溥或朝鲜的内容也并不少见。在日译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型。
(1)单纯地误记人名、地名的情况
在《通俗漂海录》中,虽然不能清楚地知道误译是译者的错误还是刻匠的失误造成,但在人名和地名中,可以发现大量误字,如下表。
续表
除此之外,对《漂海录》中出现的人名,《通俗漂海录》中仅以“某”来代表。比如2月18日的“太监某”实际是“太监罗”,5月17日的“总兵某”实际是“总兵官缑谦”,6月朔日的“千户某氏”应为“千户董文”。
(2)在翻译中,对原文的错误解释
译者在翻译中,由于缺乏准确性,在解释时犯下错误的地方如下。
(3)在原文中润色或添枝加叶的地方
清田君锦为了使翻译更加顺畅,润色或添加了原文中根本就没有的句子。同时,又特别用心地避开了一些特定词语。比如将“倭”或“倭贼”改为“海贼”;将“倭船”改为“外国船”,想瞒下“海贼”就是“日本海贼”的事实。这样的例子在闰正月19日有4处,闰正月21日有2处,2月9日有1处。因此把为了防备倭寇侵入而设置的明朝官职“把总松门等处备俊指挥”翻译为“指挥官”。同时,与上述润色不同的是,清田君锦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甚至插入了原书中根本没有的句子,情况如下。
(4)译者没能很好地理解的情况
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在各处附上“考”以帮助读者理解,同时又在“考”之外,在原文中附上了短小的注释。但是在这些“考”的说明中,有一些内容是清田君锦理解错了很多事实。这样的例子,比如卷首的“考”中,对朝鲜历史进行了概述,有“至明初,宰相李仁人灭君主王氏,篡高丽改国号为朝鲜至今”的部分。这是因为参考了原来就发生了错误的中国史书,可能清田君锦参考了最先发生错误的《大明会典》中明太祖的《皇明祖训》。另外,3月7日记载“山之奇峻,闽之黄山天下第一……”条目中,其实黄山不在“闽”即福建,而是位于安徽的天下名山。
(5)歧视崔溥或朝鲜的情况
最后是清田君锦歧视朝鲜或崔溥本人的部分,在翻译本中随处可见。因为这是反映18世纪日本儒学者的朝鲜观的实例,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对于这一问题,牧田谛亮已经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似无赘述必要,仅以简略的概述一带而过。
仅是通过观看上述几例来看,清田君锦对崔溥和朝鲜的歧视态度格外明显,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日本优越的民族意识。事实上,在翻译中,也犯下不少错误的清田君锦,在别人评论他的文章粗糙时,用以下贬低之词进行辩解。
序文:先生购朝鲜崔溥之《漂海录》阅后曰:“文章虽有朴陋之嫌,亦可为异域风土之证。”[17]
附言六条:乃曰。文虽朴陋。其于异域风土。亦可以证也。[18](www.chuimin.cn)
崔溥一行在经历了13天的漂流后,漂落到了浙江的海岸,登陆之后,在那样迫切和艰难的情况下,为留下简单的笔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这样零碎的记录为基础,一回国就奉成宗之命,撰写了《漂海录》。当然,对于崔溥推迟奔丧之后,仅在8天之内撰写完毕的事实,清田君锦当然是不会知道的。清田君锦的评价,未考虑到崔溥以漂流人受问,又被遣送回国的身份,因而评价有失公正。
我们再看看《 (漂海录)》的译文,就会发现这不是全译,而是节译。文中不仅有大量的省略和压缩之处,误译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对于原本的保存状态并不太好的《
(漂海录)》的译文,就会发现这不是全译,而是节译。文中不仅有大量的省略和压缩之处,误译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对于原本的保存状态并不太好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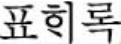 (漂海录)》,尹致富付出了大量努力进行了注解,并指出了大部分文中的谬误。[19]我们在此仅对遗漏的几处误译进行了整理,如下表。
(漂海录)》,尹致富付出了大量努力进行了注解,并指出了大部分文中的谬误。[19]我们在此仅对遗漏的几处误译进行了整理,如下表。
4.《通俗漂海录》和《 (漂海录)》比较
(漂海录)》比较
《漂海录》的作者崔溥,作为性理学者,精通历史和地理,曾在成宗十六年(1485)帮助徐居正编纂了《东国通鉴》,第二年帮助金宗直编纂了《东国舆地胜览》,并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恰巧清田君锦也是性理学者,他也有渊博的历史和地理学知识,他有包括十卷《资治通鉴批评》在内的诸多历史著作。这在他的弟子柚木太玄写的“通俗漂海录序”之后的论评中可以看到。
先生尤精史学。其谈史,唐虞迨明请。若目亲见其域世焉。其可旁以及证异域舆地。亦若足亲履其地焉。[20]
另外,崔溥在《漂海录》5月28日中写下“辽东……五代时虽为渤海大氏所据,后为辽、金、元并吞”这样多多少少不准确的文字,对此清田君锦吹毛求疵道,“渤海国之大氏,中唐时势力炽盛,备百官之制,俨然为一国之主也。五代之初,受辽侵寇而衰。崔溥之言,误也”。另外,《通俗漂海录》的译者清田君锦是持有国粹主义立场的儒学者,他这样的思考,在“附言六条”或“考”中也反映得一清二楚。
旧时中国亦称蕃戎,今日妄自菲薄卑称倭俗,以旧时蕃戎之国名以中华·中夏,良可叹矣。[21]
凡天地间无可匹于大日本者也,不可不明。[22]
文录役(壬辰倭乱)之时朝鲜王亡命于义州。吾大日本军,未追踪至彼,其之天幸,可称额矣。[23]
18世纪的日本知识人具有的两面性中,一方面是歧视朝鲜,同时另一方面,曾极尽全力款待朝鲜通信使的事实,我们也要充分重视。
18世纪后半期以来,日本人通过清田君锦翻译的《通俗漂海录》,可以比较容易地阅读崔溥《漂海录》。但是相同时代,在朝鲜仍然只有用汉文撰写的《漂海录》,仅有一部分阶层可以阅读。在朝鲜进入19世纪后,虽然也出现了手抄的谚解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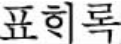 (漂海录)》,但是几乎没有韩文《
(漂海录)》,但是几乎没有韩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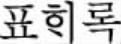 (漂海录)》的刊印本存世。可以对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
(漂海录)》的刊印本存世。可以对日译《通俗漂海录》和谚解本《 (漂海录)》进行比较,但是把两者进行直接比较还是有不合理的地方。日本的《通俗漂海录》是18世纪的出版刊印物,但是朝鲜的《
(漂海录)》进行比较,但是把两者进行直接比较还是有不合理的地方。日本的《通俗漂海录》是18世纪的出版刊印物,但是朝鲜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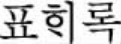 (漂海录)》只是19世纪的手抄本而已。《通俗漂海录》虽然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书店出版的“坊刻本”,但是《
(漂海录)》只是19世纪的手抄本而已。《通俗漂海录》虽然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书店出版的“坊刻本”,但是《 (漂海录)》就连谚解者是谁都不清楚,仅知道是“止庵公朴夫人”的遗墨,就连这份手抄本也是仅存留一半而已。
(漂海录)》就连谚解者是谁都不清楚,仅知道是“止庵公朴夫人”的遗墨,就连这份手抄本也是仅存留一半而已。
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把两者作为比较对象放在一起的原因,是要通过比较了解一下18—19世纪朝鲜和日本两国出版印刷文化的面貌。出版了日本《通俗漂海录》的“书肆”是一家盈利出版社,日本的《通俗漂海录》相当于朝鲜的所谓坊刻本。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朝鲜在相同时期内没有出现坊刻本《 (漂海录)》,而是继续放在崔溥文集《锦南集》之中出版刊行。
(漂海录)》,而是继续放在崔溥文集《锦南集》之中出版刊行。
朝鲜的坊刻印刷,以宣祖九年(1576)出版的《故事撮要》为源头,最后章内刊刻有“水标桥下,北部二第里门入口的河汉水家刊刻木版,求购者可来”的内容。但是这无论如何只能算是起源而已,在朝鲜坊刻本印刷盛行实际上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24]
17世纪,朝鲜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在战火中失去的书籍,需要应急性地补充,因此需要廉价出版坊刻本。但是18世纪英祖、正祖时期,中央有官板活字本盛行,地方有木活字,因此对坊刻本的需要,并不强烈。到了19世纪,一般大众也对书籍有了较大需要,以盈利目的出版廉价坊刻本,大为活跃。[25]
夫吉万把朝鲜时代的坊刻本出版时期,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第1期:强调实用性(1576—1724)
第2期:强调儒教修养和儿童的学习(1725—1842)
第3期:娱乐功能的强化和实用性的扩大(1843—1910)
尤其是把第三期特征,定为“不仅是士大夫家门的的妇女子,平民层中也出现了扩大的读书层,多种多样内容的小说开始出现。到这时为止,以儒教修养或学习目的出版的坊刻本,开始以娱乐的目的出版。即,坊刻本小说开始出现。”[26]推定为谚解本《 (漂海录)》的手抄本时间的高宗十年(1873),就是第3期的中期。当然崔溥《漂海录》在鱼叔权撰写的《稗官杂记》中被提及,“在我东国缺少小说,仅台谏李仁老之《破闲集》……校理崔溥之《漂海记》,海平郑眉寿之《闲中启齿》,忠庵金净之《济州风土记》,适庵曹伸之《谀闻琐录》,传于世”,[27]崔溥《漂海录》被当做“小说”,受到世人关注。[28]
(漂海录)》的手抄本时间的高宗十年(1873),就是第3期的中期。当然崔溥《漂海录》在鱼叔权撰写的《稗官杂记》中被提及,“在我东国缺少小说,仅台谏李仁老之《破闲集》……校理崔溥之《漂海记》,海平郑眉寿之《闲中启齿》,忠庵金净之《济州风土记》,适庵曹伸之《谀闻琐录》,传于世”,[27]崔溥《漂海录》被当做“小说”,受到世人关注。[28]
在19世纪,在朝鲜虽然盛行坊刻本小说,但是始终没有出现韩文《漂海录》坊刻本。但是在日本,18世纪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出版社出版了坊刻本《通俗漂海录》,并在原本中添加了41个小标题和多幅插图。清田君锦的二哥江村绥写的题言中,提到了下面重要的事实,“书肆某请弟君锦。抄略其书。译便幼学。又求余题言。”[29]
这家叫皇都书林的出版社,先决定翻译和出版《漂海录》,然后确定了最适合的译者清田君锦后,与他进行了接触。不能不说,这是18世纪日本出版印刷文化状况的最好实例。把日本的《通俗漂海录》和朝鲜的《 (漂海录)》进行简单的比较,如下表。
(漂海录)》进行简单的比较,如下表。
在朝鲜为什么没能出现《 (漂海录)》坊刻本,我们以几个假设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在日本坊刻本出版非常活跃的18世纪,是朝鲜坊刻本出版相对萎缩的时期。即,受朝鲜英祖、正祖时代官板本活跃的影响,这是一个坊刻本相对较少的时代。但是在19世纪朝鲜的坊刻本出版活跃的时候,也没有出现《
(漂海录)》坊刻本,我们以几个假设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在日本坊刻本出版非常活跃的18世纪,是朝鲜坊刻本出版相对萎缩的时期。即,受朝鲜英祖、正祖时代官板本活跃的影响,这是一个坊刻本相对较少的时代。但是在19世纪朝鲜的坊刻本出版活跃的时候,也没有出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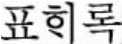 (漂海录)》的坊刻本。
(漂海录)》的坊刻本。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朝鲜王朝保持以王室为中心的书籍出版政策,使得朝鲜保持了保守的传统。[30]同时,可以提出否认书籍为商品化的想法。中宗二十四年(1529),以大司谏鱼得江向中宗提出的建议为中心,君臣们展开了如下的讨论。
得江曰:“我国之人,无长久悠远之计,凡立法、行事,例皆取办龄目前。大抵礼乐,必积德百年而兴,至龄法令,亦非朝令而夕行也。我国人心,今日立法,而明日欲行,故法不能行也。臣前为掌令时,以书店设立事启之。人皆以为,非所当启而启之,此事不必行于一二朔内也。虽至十年或百年而行之,无妨也。世家、大族,或有祖上传来之书,或有受赐之书,而反为无用之物者,必多有之。若立书店,则欲卖者卖之,欲买者买之。为儒者,若毕读一册,则卖其册,而买他册读之。交相买卖,以为悠久之计矣。古人云:‘借书痴,还书痴。’世人以卖祖上传来之书,为非而不肯为之。然束之高阁,一不披读,其为蠹虫之食,亦何益哉?外方之儒,虽有志于学,以无书册,不能读书者,亦多有之。其穷乏者,不能办价买册,而虽或有办价者,如《中庸》、《大学》,亦给常緜布四三匹买之。价重如此,故不能买之。若书店之册,则量定其价,又设监掌之员,而通行买卖,传于永久,可得无弊矣。古人家贫无册者,阅书于市肆,而成功者有之。今设书店,出置书册,则有志者,虽不买读,终日披阅,犹可记忆矣,至为便益。请令该曹磨炼设立。”上曰:“此事前亦议之,皆以为不可。以他馀市肆见之,则此果有益。向学之人,无书册而未读者,必多有之。予意亦以为,书店可设立也。但立前古所无之事,其举行与否,未可知也。”[31]
三公启曰:“书店设立事,名似崇文,果为好矣,但国俗所未曾为之事也。且如寡妇之家,虽或有卖书册者,其私相买卖之事,必为之矣,出置于书肆,则恐不为也。书册比处,不为措置,而徒设书店,则法何由行。大抵可行之法,则立之当矣,不可行之法,则立之非徒无益,反为有害。臣等之意,此事在所不当为也。”[32]
对于鱼得江打算设立书店流通书籍的提议,中宗基本表示同意的同时,说道“前所未有之事,是否实行未可知也”,三公也以“我国风俗未有之事”为由来反对。这最好地反映了16世纪,朝鲜书籍未能以商品形式进行流通的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18世纪“商业发达”形成的朝鲜后期,作为商品的书籍坊刻本的出版比日本沉寂的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金东旭下面的说明,给我们的启示非常大。
这样小说的坊刻本的出现比中国或日本晚,是朝鲜可以读小说的读书阶级的形成缓慢的最好证明。即,就算是中人阶级,其数量也是有限的,两班家的妇女子更依靠手抄本;而以胥吏、军官为中心的低级的读书阶级的形成,是更晚的事情了。和日本江户时代的板本小说《读本》、《黄表纸》等的需要源町人阶级相似的我国的商人阶层,财富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33]
18世纪朝鲜后期的“商业发达”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商业发达”,经常被相提并论,我们不得不提出两国18世纪的“商业发达”实质是否一样的疑问。虽然这一问题要在社会经济史领域进行正式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出版印刷文化的面貌也根据商业发达的面貌,在两国之间有所差异。另外,不仅日本的人口比朝鲜多,而且读书人口的比例比朝鲜自然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只能通过海洋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岛国日本人,对“通过海洋活动而得到的外国故事”,比同一时代的朝鲜人会更感兴趣。
小 结
传到日本的崔溥《漂海录》,在英祖四年(1769)被儒学者清田君锦译为《唐土行程记》一书,26年后改题为《通俗漂海录》。在京都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唐土行程记》和《通俗漂海录》,国立中央图书馆也收藏了这两本书,虽然从内容上看,没有什么差别,但从目录的排列看,四部均有略微不同。改题的《通俗漂海录》作为译本更为适合,以后在学术界应该以《通俗漂海录》来统一称呼。
《通俗漂海录》的译者清田君锦,为把中国的相关知识以通俗方式传达给日本人,将原书压缩后进行了翻译。在朝鲜只能是一部分“识字阶层”的人们能阅读以汉文撰写的《漂海录》时,日本的庶民百姓已经从18世纪后期开始就可以用日本语来阅读《通俗漂海录》。朝鲜也从19世纪后期出现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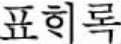 (漂海录)》谚解本的手抄本,但是这本书的谚解与手抄时间,已经是高宗十年(1873)以后的事情了。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
(漂海录)》谚解本的手抄本,但是这本书的谚解与手抄时间,已经是高宗十年(1873)以后的事情了。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 (漂海录)》手抄本曾经以刊印本出版流通。
(漂海录)》手抄本曾经以刊印本出版流通。
《通俗漂海录》的译者清田君锦,在翻译上有大量的错误,同样,无法确认译者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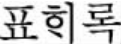 (漂海录)》谚解本,也存在大量错误。另一方面,清田君锦以论评“考”,展示了他的博识,但是也把他的国粹主义的面貌暴露无遗。虽然我们知道一些逸话,说在18世纪日本人为了得到诗文,特别殷勤地接待过朝鲜通信使;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时以一部分国粹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朝鲜歧视的思潮。
(漂海录)》谚解本,也存在大量错误。另一方面,清田君锦以论评“考”,展示了他的博识,但是也把他的国粹主义的面貌暴露无遗。虽然我们知道一些逸话,说在18世纪日本人为了得到诗文,特别殷勤地接待过朝鲜通信使;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时以一部分国粹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朝鲜歧视的思潮。
《通俗漂海录》一开始就被商业利润驱使的书店(书肆)出版,相当于朝鲜的“坊刻本”。崔溥《漂海录》虽然在18世纪已经在日本以坊刻本的形态出版,但是在朝鲜,到了19世纪也没有出现坊刻本的《 (漂海录)》。坊刻本在出版印刷领域,是商业化进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谚解本《
(漂海录)》。坊刻本在出版印刷领域,是商业化进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谚解本《 (漂海录)》仅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保存了一本粗糙的手抄本而已。
(漂海录)》仅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保存了一本粗糙的手抄本而已。
我们认为这是两国出版印刷的不同文化传统引起的。同时,我们可以着眼于当时两国之间全体人口的差异、可读书人口比例等问题;另外,通过海洋与外国贸易的日本人,比朝鲜人更关心海洋活动也是重要原因。最后,就如金东旭曾言,从18世纪两国不同的商业发达水准和坊刻本出版相关的视野出发,以后我们需要在出版印刷文化史中,对该课题进行更深的比较研究。
【注释】
[1]清田君锦本名为“绚”按理应称为“清田绚”但是在日本儒学史使用“儋叟”这样的号,因此一般被人称为“清田儋叟”。另外,写下关于《唐土行程记》首篇论文的牧田谛亮以字称之,曰“清田君锦”。《唐土行程记》的题文、序文、跋文中又写为“清君锦”在书店的刊记中也记为“清君锦先生”。另外,清田君锦本人在“附言六条”末尾和各卷的卷首将自己的名字称为“清绚”。为了避免同一人物多个姓名引起的混乱,在本文中将统一使用“清田君锦”这一名字。
[2]牧田谛亮,《唐土行程记谈义》,《神田喜一郎先生追悼中国学论集》,京都二玄社,1986年,第610—624页。日本的牧田谛亮教授将本人保存的《唐土行程记》复印本在1995年赠送给了北京大学的葛振家教授,而笔者在同一年,又从葛振家教授那里得到了复印本。
[3]参考这本书的第1部1章《崔溥〈漂海录〉版本考》。
[4]从高氏保存的手抄本收录了柳希春的“隆庆三年跋文”和“万历元年跋文”来看,这是肃宗三年(1677)出版刊行的奎章阁本的手抄本的可能性非常大。当然“崔希春”是“柳希春”的单纯错误。
[5]《唐土行程记·旧跋》:“锦南崔先生讳溥,字渊渊,希春之外祖父也。以经术气节遭遇成庙,擢置侍从尝奉命往耽罗。适奔父丧,为风所逆,漂到中国之台。还至都城外,上命撰进一行日录,览而嘉之,遂俾藏于承文院。其文字,卷不过三,而不唯状大洋变化。自瓯徂燕,一路山川、土产、人物、风俗,粲然森列,而先生经济之才,亦可得其什一。求多闻务博览之士,愿见者众矣。而至今八十年间,未有锓梓以广其传者。希春自塞外蒙恩还朝,亟思所以寿是书者,校正既了,唯以主张措画为难得。会博雅吴公出按关西,希春以书恳属。公遂欣然而诺,定州守尹侯行鸠游手完其役,而讫于成。噫!是书残缺沈沦且百年,今乃得显放久晦之馀,将大行于斯世,岂非幸也欤?隆庆三年龙集己巳八月既望,外孙通政大夫成均馆大司成知制教柳希春谨识。”(标点:笔者)
[6]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京都法藏馆,1959年,第234页。
[7]参考本书的第1部2章《崔溥〈漂海录〉校勘记》。
[8]《唐土行程记》卷二,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影印本,2月8日。
[9]《唐土行程记》卷一,“考”:“此书ノ原本ハ朝鲜ノ崔溥ガ撰セシ所ニテ。漂海录ト号ス。然レモ唐土里程ノ事ヲオモニ记セルニ因テ。今ノ名ニ改ム。”
[10]牧田谛亮,《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记》《金泽文库研究》第272号,神奈川县金泽文库,1984年,第23页。
[11]笔者向京都大学文学部夫马进教授请求,在2003年得到了京都大学图书馆《通俗漂海录》复印本。
[12]牧田谛亮,前揭论文,1986年,第609页。
[13]崔溥著、播磨清绚译,《唐土行程记》,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古典运营室,请求记号韩古朝63—42;《通俗漂海录》,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古典运营室,请求记号韩古朝63—53。
[14]点苍山是位于云南的名山,清田君锦仅在为帮助读者理解而写的“考”中提及,在崔溥《漂海录》的原书中绝无提及。
[15]曺永禄,《关于近世东亚三国的传统社会比较史的考察——以崔溥的〈漂海录〉和日译〈唐土行程记〉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64辑,1998年,第1—14页;《近世东亚细亚三国的国际交流与文化》,知识产业社,2002年,第175—205页;宫岛博史,《对崔溥〈漂海录〉的日译〈唐土行程记〉的研究》,《大东文化研究》第56辑。
[16]尹致富,《注解 ·解题》,图书出版博而精,1998年,第1—2页。
·解题》,图书出版博而精,1998年,第1—2页。
[17]《通俗漂海录·序》。
[18]《通俗漂海录·附言六条》。
[19]尹致富,前揭书,第2—3页。
[20]《通俗漂海录·序》。
[21]《通俗漂海录·附言六条》。见べシ吾国の古へハ。唐土ヲモ蕃戎トヨバセ玉ヒシコトヲ。イカナレパ今ノ人ハ。吾国ヨ倭俗ト鄙シメ。彼蕃戎トヨバヤ玉ヒシ国ヲ中夏ナド尊称ス。吾国ノ法令ニ畔ノ甚シキトイフベシ。
[22]《通俗漂海录》卷二,闰正月21日。凡ソ天地ノ间。吾大日本ニ及ノ国ハ。决メナキト知ベシ。
[23]《通俗漂海录》卷四,6月4日。文录ノ役。朝鲜王义州ヘ逃入ル。吾大日本ノ兵ノソレマデ追付ザルハ彼国ノ天幸トイフベシ。
[24]千惠凤,《韩国书志学》改订版,民音社,1997年,第232页。
[25]金东旭,《关于坊刻本》,《东方学志》11辑,1970年,第97—139页。
[26]夫吉万,《朝鲜时代坊刻本之出版研究》,首尔出版媒体,2003年,第34—37页。
[27]《大东野乘》卷一,《稗官杂记》第四卷,民族文化推进会古典国译丛书DB。
[28]国立中央图书馆书志学部《朝鲜书志学概观》,国立出版社(平壤),1955年,第202页,韩国文化社1999年影印本现在仍然把崔溥的《漂海记》放在稗官文学的范畴内。
[29]《通俗漂海录·题言》。
[30]韩东明,《对朝鲜初书籍出版政策的考察》,《庆熙史学朴性凤教授回甲纪念论丛》,庆熙大学校,1987年,第446页。
[31]《朝鲜中宗实录》,中宗二十四年5月己未。
[32]《朝鲜中宗实录》,中宗四年5月庚申。
[33]金东旭,《关于坊刻本》,《东方学志》11辑,1970年,第108—109页。
有关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的文章

2章崔溥《漂海录》校勘记引言1. 6种版本的对校2.对校结果的分析3.对中国文献的校勘小结引言在朝鲜时代,崔溥《漂海录》在壬辰倭乱之前和之后,各出版3次。崔溥《漂海录》有6种版本之多,非常有必要通过对校,对文字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调查。1964年,在金灿顺第一次节译了崔溥《漂海录》。笔者先对崔溥《漂海录》的6种版本,进行了对校,想在决定研究所需底本时,留下确实的根据。......
2023-11-30

[4]李载浩,《漂海录》,《国译燕行录选集》,(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古典国译丛书,1976年。[6]崔周容,《漂海录》,(首尔)极东精版社,1984年。[8]葛振家主编,《崔溥漂海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朴元熇,《崔溥漂海录研究》,(首尔)高丽大学校出版部,2006年。[13]朴元熇,《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2023-11-30

但是崔溥《漂海录》中,除了以上的3种版本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版本。为了崔溥《漂海录》的完美的译注,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开展研究,对版本的调查必须先期进行,这一重要性是必须重复的。而且,通过这一过程选择最为适合的版本,作为译注的底本,这也是笔者为了开拓研究,对崔溥《漂海录》版本不得不亲力亲为进行考察的重要原因。......
2023-11-30

1章崔溥《漂海录》研究述评1.初期之《漂海录》研究2.《漂海录》的4种韩文译本3.《漂海录》研究之扩散4.《漂海录》特辑和探访记5.最近的《漂海录》研究动向1.初期之《漂海录》研究崔溥是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在1958年,Meskill就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以英文译注本崔溥《漂海录》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申请了博士学位。既不是在韩国,也不是在日本,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出现了对崔溥《漂海录》的最初研究成果,的确是出乎意料之事。......
2023-11-30

《唐土行程记》在初版26年后,改名《通俗漂海录》再次出版。最新出版的韩文翻译本是2004年出版的徐仁范、朱圣志的《漂海录》。另外,牧田谛亮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译注工作,但是以阳明文库本的《漂海录》......
2023-11-30

探访游记:沿着崔溥的足迹1.韩国人为什么不知道崔溥?在漫天灰尘中,奔驰的汽车内,忍受着颠簸,在脑子中却是装满了,寻找朝鲜时代历史人物崔溥足迹的想法。与死亡进行了13天殊死搏斗之后,最终崔溥一行乘坐的海船漂流到中国浙江省的某个海岸。在杭州接受了最终调查的崔溥,为了返回朝鲜,通过大运河被移送到北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之后,出人意料地受到明朝皇帝的赏赐。......
2023-11-30

3章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以崔溥《漂海录》为路标引言1.对朝鲜文化的理解2.对朝鲜历史的认识3.对朝鲜人物的关心小结引言为了考察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我们广泛查阅了同时代的中国和朝鲜文献。因此,明代中期记录的崔溥《漂海录》,虽然不能视为典型的《燕行录》,但是它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在15世纪的有关大运河旅程的记录中,崔溥《漂海录》的准确性和详细程度,当然是首屈一指的。......
2023-11-30

十五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日记体著作,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富有学术价值。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运河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又完整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之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因而弥足珍贵,颇具价值。崔溥在杭州待了七天,经由坝子桥入京杭大运河回朝鲜。......
2023-10-31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