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章崔溥《漂海录》校勘记引言1. 6种版本的对校2.对校结果的分析3.对中国文献的校勘小结引言在朝鲜时代,崔溥《漂海录》在壬辰倭乱之前和之后,各出版3次。崔溥《漂海录》有6种版本之多,非常有必要通过对校,对文字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调查。1964年,在金灿顺第一次节译了崔溥《漂海录》。笔者先对崔溥《漂海录》的6种版本,进行了对校,想在决定研究所需底本时,留下确实的根据。......
2023-11-30
1章 崔溥《漂海录》研究述评
1.初期之《漂海录》研究
2.《漂海录》的4种韩文译本
3.《漂海录》研究之扩散
4.《漂海录》特辑和探访记
5.最近的《漂海录》研究动向
1.初期之《漂海录》研究
崔溥(1454—1504)是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他在济州担任推刷敬差官时,在成宗十九年(弘治元年,1488)因父亲突然去世,急忙乘船回家途中,不幸遇风浪,在13天的海上漂流之后,最终在中国的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海岸登陆。崔溥一行43人在受到各种苦难之后,被确认为是朝鲜人之后,被押送到杭州,之后经过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短暂休息之后,经过辽东最后回到朝鲜。《漂海录》是崔溥到达汉阳之后,根据朝鲜王成宗之命写下的报告书,将一行从漂流开始,在中国的旅程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下来的中国见闻录。当时作为朝鲜人,到达中国江南是少而又少的事情,对中国见闻的记载,轰动了朝鲜朝野上下。
对崔溥《漂海录》[1],第一次表明了学术性关心的,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叫Meskill的美国学者。在1958年,Meskill就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以英文译注本崔溥《漂海录》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申请了博士学位。既不是在韩国,也不是在日本,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出现了对崔溥《漂海录》的最初研究成果,的确是出乎意料之事。美国学者通过怎样的途径知道了崔溥《漂海录》,并进行了英文翻译,这个疑团随着Meskill在1950年代曾经是日本留学生这一点,被人了解后,成为解开疑团的线索,一点点被人所知。在20世纪50年代,Meskill留学日本,在此生活的两年期间,从恩师宫崎市定教授那里知道了崔溥《漂海录》的存在。[2]
在这一时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牧田谛亮也对1 5世纪日本僧侣策彦的《入明记》进行着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朝鲜人崔溥在策彦之前的51年,已经走过了和策彦相似的中国旅行之路,并留下了崔溥的《漂海录》这本见闻录。并且牧田谛亮将此研究成果以《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为题,分上下两册出版,在第7章《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记》中,对崔溥和《漂海录》以及18世纪时清田君锦翻译为日文的崔溥《漂海录》,即《唐土行程记》,进行了简略地介绍。在策彦《入明记》的研究过程中,对崔溥《漂海录》产生了关心的牧田谛亮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译注,但以阳明文库本《漂海录》为原本,对原文进行了断句和标点,崔溥《漂海录》原文以参考文献形式,被收录在他的著作《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中[3]。
不久之后,高柄翊在《Meskill〈锦南漂海录〉译注》书评中,对Meskill进行英文翻译时,误译较少的理由进行了分析,指出“而且似乎上面列举的《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中,已经断句和标点的原文收录之故,其误读可能已经较少”的推测。另一方面,原先对Meskill的《漂海录》英译本,毫不知情的牧田谛亮也通过高柄翊的书评知道了这一事实,在他的另一篇论文《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记》的末尾部分,添加“漂海录の英译につぃて”,说出了下面的一段话。
Meskill氏曾经来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虽然向我表达了想翻译《策彦入明记之研究》的想法,但是最终译注了《漂海录》并以此作为学位论文,提交到哥伦比亚大学。《策彦入明记之研究》在昭和三十四年(1959)3月已经完成,估计他已经看过这本书,高教授也曾经指出英译本中误译较少的原因是参考过《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中已经标注过标点符号的《漂海录》(或许也有些误读,本人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读过原文之后,考虑进行慎重的对应。[4]
但是以上两位这样的推断,是根据Meskill的Ch’oe Pu’s Diary: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一书出版于1965年为准进行的推断而已。在1965年出版的这本书是在1958年他本人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了少许补充出版的。因此,判断Meskill是否曾经参考过牧田谛亮的著作,应该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提交时间为准进行判定。事实上,《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上)》的出版时间是1955年,比Meskill的博士学位论文早了3年之多,但是收录了《漂海录》的《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的出版时间是1959年,反而比Meskill晚了1年。因此,当时留学日本并和牧田谛亮见过的Meskill,如果假设他得到了《漂海录》的断句标点版本的话,那个时间是几年前牧田谛亮进行了断句标点的稿件,只有这样从时间上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对此,Meskill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序言中,对牧田谛亮的稿件,没有一言半语的提及。从以上几种情况分析来看,Meskill在英译开始之前,先得到牧田谛亮的《漂海录》断句原稿,并在英译前使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与其注意牧田谛亮已经做了断句标点的《漂海录》稿件,不如关注当时Meskill有可能使用《漂海录》断句标点资料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日本京都的阳明文库保存的木版本《漂海录》。Meskill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去过京都的阳明文库和横浜的金泽文库,还有东京的东洋文库和内阁文库,针对《漂海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基础性的版本调查,对这一点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序言中,并无讳言之处。但是,Meskill在50年代,去过阳明文库和金泽文库的证据,笔者偶然从另外的渠道中证实。2002年10月笔者访问金泽文库,在查看这里收藏的金泽文库本《漂海录》时,在书的最后葛皮中,发现了一张插着的介绍信。这张信是当时东京都立大学森克己教授给金泽文库的熊原政男文库长写的,其中谈到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当时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Meskill访问的话,在查阅资料时,请提供便利的内容,写于6月16日。还有写下阳明文库所藏《漂海录》跋文的两张稿纸,在稿纸的片头位置上,有用红笔写下了“哥伦比亚大学Meskill告诉我文库”的字样。从这里可以看出Meskill先在京都阳明文库做了《漂海录》版本调查之后,路过东京,到达了横浜金泽文库。在这样的版本调查过程中,在阅览过阳明文库本《漂海录》后,曾经收藏过这本书的近卫家的某个人物,在阅读《漂海录》时,用红色墨水留下了鲜明的断句标点。因为据说Meskill曾经复印过这份资料,可能在英译过程中,参考过前人已经做出的断句和标点。除此之外,Meskill可以参考的资料仍可找到,那就是在18世纪日本的清田君锦用日文翻译的《漂海录》,即《唐土行程记》。虽说《唐土行程记》不是完译本,仅为抄译稿,但是在Meskill掌握《漂海录》内容过程中,比做了断句和标点的阳明文库本,更为有用。事实上牧田谛亮也复印了阳明文库本作为底本,他在做断句和标点作业时,已经做了红墨标点的阳明文库本自然成为参考的重要内容。而且《唐土行程记》的翻译本也会自然成为参考对象。因此,Meskill或牧田谛亮均参考了这两份资料,从这一点上讲二者彼此彼此而已。无论是承认从阳明文库本《漂海录》中,还是从《唐土行程记》获得帮助,对于Meskill的《漂海录》英译本而言,终究不能贬低其价值。Meskill首次以英文完整地翻译了《漂海录》,不仅有详细的说明,而且还标注上了大量注释,同时对日本保存的数种不同版本的《漂海录》做了基础性调查,从版本角度,比牧田谛亮提及的时间还要早一年。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保存的东洋文库本、阳明文库本、金泽文库本《漂海录》,这些早期的3种版本,在韩国没有任何地方保存有全本。对版本问题,笔者在后面还要提及,在韩国保存的奎章阁本、藏书阁本不过是《漂海录》的第4和第5次的朝鲜后期版本而已。
不管怎么说,在韩国首次用韩文翻译《漂海录》之前18年,已经出版英文翻译本这件事本身,也是让人惊叹不已。Meskill以此为基础,在1965年修改后以Ch’oe Pu’s Diary: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这一题目,正式出版刊行。[5]这本书是把当初翻译的博士学位论文或多或少进行了压缩,省略了论文中罗列的长长的地名。对这本书,高柄翊有一篇指出了Meskill的几点误译的亲切而友善的书评。[6]对崔溥《漂海录》的最初的学术性关心,就是这样从美国学者Meskill和日本学者牧田谛亮开始的。在韩国郑炳昱于1961年发表了《漂海录解题》,但是这是其他种类的《漂海录》,是与张汉喆《漂海录》相关联的文章。[7]1962年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撰《燕行录选集》[8]时才在其间包含了崔溥《漂海录》,由此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漂海录》为研究对象的第一篇专门性的学术论文,由高柄翊在1964年发表。[9]这篇论文指出了《漂海录》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点基本性问题——例如:①漂流②丧服中的伦理③夷人和倭贼④相互的知见⑤撰进的是非,这些问题提出之后,成为《漂海录》研究中的基石,具有先驱性研究意义。
金炳夏在1973年作了崔溥《漂海录》和《哈梅尔漂流记》的比较研究,将崔溥和哈梅尔看到的社会面貌、意识构选和差异进行了比较。[10]不久之后,庆熙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在《韩国研究资料丛刊(4)》中,影印出版了《漂海录》。以100部限量版进行了发行的这部《漂海录》是以日本内阁文库保存的手抄本(笔写本)为底本的。这份手抄本是阳明文库本为底本进行手抄的。金炳夏在《对崔溥之漂海录》的解说里,对《漂海录》的主要内容和崔溥这一人物进行了简单的介绍。[11]
2.《漂海录》的4种韩文翻译
有关崔溥《漂海录》的第一篇研究论文由高柄翊发表于1964年,同年在朝鲜由金灿顺将《漂海录》用韩文翻译出版,[12]这成为了第一份韩文翻译,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它不是完整的翻译,而是节译(抄译)。它被放在《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9》之《纪行文集(1)》中,由此可以看出,《漂海录》是被作为文学作品之一来处理的。该韩文翻译本后来又进行了修改后于1988年再版。[13]虽然不是完整的翻译本,用了多种朝鲜使用的固有韩文语汇,但也是有益的。此后,虽然不知道准确的年代,在中国的延边以许文燮之名出版的《纪行文集》中,将崔溥《漂海录》以《漂海纪》为题收录其中。得到这本书的出版社海努里在1994年又一次出版,在首尔发行了《纪行文集》。[14]另外,中国的民族出版社也在《纪行文集》中收录了《漂海录》。[15]对这两种《漂海录》进行研讨的结果来看,笔者只能断定为,他们只是稍微地修改了朝鲜金灿顺的翻译本,事实上是按原样照抄而已。
到了1976年,李载浩的第一部完整的翻译本面世了。[16]作为民族文化推进会的《古典国译丛书》之一,出版《国译燕行录选集》时,李载浩承担了《漂海录》翻译事宜。李载浩在这次翻译中,虽然没有添加充分的注释,但是在翻译中下了大功夫的痕迹可谓处处可见。他使用的底本是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中的《漂海录》,这是藏书阁影印本,虽说他是一位汉文学者兼韩国史学者,但是因为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书中还有一些无法避免的误译,这些部分占了相当的数量。
第二次的韩文完译本是1979年由崔基弘翻译的,以非卖品形式刊行,第三次韩文完译本是1984年由崔周溶完成的,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崔基弘的译本也是以藏书阁本为底本,崔周溶译本是以全南茂安生活的崔溥的十五代孙崔正祚保存的手抄本为底本进行的翻译。[17]这些完译本均有不少误译,而且似乎不知道有先期出版的李载浩的译本,在翻译中丝毫没有参考过的痕迹,这一点相当奇特。但是无论如何,依据两位并非专业人士出身的业余研究发表的《漂海录》翻译本的出版,却成为了专业研究人员们更加努力奋发的契机。尤其是崔溥的旁系后裔崔基弘的翻译本经过修改,出版了两次改正版。[18]在首次出版10年后,崔基弘改正版《锦南先生漂海录》中,小说家李炳注写了序言。又过了8年,再次出版的修正版崔溥《漂海录》中,和李炳注的推荐辞一起的还有北京大学葛振家的推荐辞。同时书中加上了大量照片,是1994年译者沿着崔溥的足迹探访中国时留下的摄影资料,因为考虑到韩国年轻一代读者阅读的便利,译文翻译得更为通俗易懂,但是仍留有一些误译。
3.《漂海录》研究的扩散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漂海录》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开始连续不断地出现。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在1981年出版的《国语国文学事典》中,加入了郑炳昱写的《漂海录》的条目。[19]崔康贤把《漂海录》放到海洋文学的范畴,进行了文学性的分析。这篇文章,在他第二年出版的著作《韩国纪行文学研究》中,以《纪行歌辞类型的考察》为题收录入册。[20]日本的牧田谛亮发表了与《漂海录》在18世纪翻译成日文的《唐土行程记》相关的两篇论文。[21]金在先以《崔溥〈漂海录〉与明代海防》为题,发表论文,[22]此后又连续发表了6篇论文。[23]大部分论文也是把《漂海录》的叙述内容,简单地抄到文章中,就连“研究”这样的话也谈不上。另一方面,张德顺的《海洋文学的白眉〈漂海录〉》使用《朝鲜成宗实录》中记载的崔溥的口头报告,选粹了《漂海录》中富有文学性色彩的部分,进行了翻译,并加以介绍。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张德顺谈到“虽然这部漂海录已经有了日文译本(1721~1785,清田君锦译)和英文译本,并在海外广为人知,但是据本人所知,国内还没有翻译,这真是莫大的遗憾”,就算是不知道朝鲜有翻译本,但是不知道民族文化推进会的李载浩已经有译本的事实,“真的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啊”。[24]
1988年,民族文化推进会出版了《韩国文集丛刊》,将崔溥的文集《锦南集》影印后收录其中,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漂海录》。到目前为止,与韩国翻译都是以藏书阁本(英祖元年,1725)为底本相反,这《漂海录》的第一卷是以东洋文库本(中宗六年,推测刊行于1511年)为底本,第二、三卷以奎章阁本(肃宗二年,1676年)为底本。这样分开的原因是,东洋文库本在国内只有高丽大学图书馆华山文库的第一册,奎章阁本在奎章阁也仅有第二、三册的原因。当然这两个版本都比藏书阁本更早。民族文化推进会在此版本上标点出版,同时把目前为止不同的版本也一起介绍到学术界。
1991年,《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由精神文化研究院出版,其中关于崔溥《漂海录》的内容有“崔溥”、“漂海录”、“锦南集”等三个条目[25]。“崔溥”条目是由高柄翊,“漂海录”是由崔康贤,“锦南集”是由李东述他们各自编辑而成。“崔溥”的“溥”字,虽然有“宽广之溥(Bo)”、“展开之溥(Bu)”、“水纹样溥(Bak)”三种意思和发音,但是《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的三个条目中,均以“(Bo)”为发音。我感觉可能是辞典编纂委员会已经就“(Bo)”为唯一发音进行了统一。事实上在这之前崔康贤和张德顺都在各自的文章中使用了“Choe Bo”这一称呼,这始于之前执笔了《国语国文学辞典》之《漂海录》项目的郑炳昱。一般来说,考虑到辞典的权威性,就按原来的样子使用“Choe Bo”就可以,但是笔者认为这个人名有必要以“Choe Bu”来统一发音。这是因为第一,可以参考的发音,历史最久的是谚解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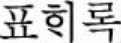 (漂海录)》中发音“Choe Bui”,“Bui”在今天相当于“Bu”这个发音。第二,耽津崔氏以“Choe Bu”为共用发音。第三,最早的韩文翻译本,朝鲜的金灿顺的译本中也以“Choe Bu”为发音。第四,韩国第一次完成的完译本中,李载浩也以“Choe Bu”作为发音,因此我认为在读历史人物的人名时,以后不应该再发生混乱。[26]
(漂海录)》中发音“Choe Bui”,“Bui”在今天相当于“Bu”这个发音。第二,耽津崔氏以“Choe Bu”为共用发音。第三,最早的韩文翻译本,朝鲜的金灿顺的译本中也以“Choe Bu”为发音。第四,韩国第一次完成的完译本中,李载浩也以“Choe Bu”作为发音,因此我认为在读历史人物的人名时,以后不应该再发生混乱。[26]
1992年景仁文化社文集编纂委员会影印了《锦南先生文集》,在其中收录了檀纪四二八七年(1954)有罗致焕序文的木活字本《漂海录》。不知道文集编纂委员会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选择了木活字本,由于没有“解题”,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判断编纂意图。1992年,中国北京大学的葛振家出版了《漂海录——中国行记》点注本,在《漂海录》中,进行了断句和标点并加以注释。收录了《〈漂海录〉初探》这样的解说,主要以弘治初期的①海禁、海防、漂流事件处理②南北交通③施政风物④通过崔溥看到的朝鲜的儒家思想为中心点,进行了叙述。[27]在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之后,中国学者也终于加入到了对《漂海录》的研究中。在这本点注本中,可以发现标点和注释有不少误谬之处。另一方面国文学者崔来沃也发表了《漂海录研究》,在海洋文学的范畴内分析了6种《漂海录》。[28]将崔溥的《漂海录》以人物、书志、韩文《 (漂海录)》为中心,进行了简要整理。崔来沃从崔康贤那里听到谚解本《
(漂海录)》为中心,进行了简要整理。崔来沃从崔康贤那里听到谚解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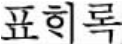 (漂海录)》保存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之后调查了19世纪的韩文谚解本《
(漂海录)》保存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之后调查了19世纪的韩文谚解本《 (漂海录)》,进行了介绍。
(漂海录)》,进行了介绍。
葛振家在这段时间内将研究《漂海录》的韩国、日本、美国、中国的8名学者的12篇文章翻译为中文,在1995年编为《崔溥〈漂海录〉研究》后出版。[29]同时,以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邀请了崔基弘、高柄翊、崔来沃、金在先、杨万鼎、牧田谛亮、Meskill等学者到达北京,举办了《崔溥〈漂海录〉研究》的出版学术座谈会。[30]葛振家同时修改了自己的点注本《漂海录——中国行记》,同时把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的两篇论文也加入其中,[31]将书名改为《崔溥〈漂海录〉评注》后再版。[32]新增的两篇论文题目是《〈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讨》和《崔溥〈漂海录〉价值再探析》。前者是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众多外国人的中国纪行记中,崔溥《漂海录》具有的价值的论文;后者是讨论在朝鲜的诸多《朝天录》、《燕行录》中,《漂海录》占据的座标性地位的论文。对崔溥《漂海录》在中国纪行记书中的价值,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
另一方面,乡土史学者杨万鼎也发表了《锦南崔溥〈漂海录〉撰进中带来的磨难和戊午士祸的考察》,这是介绍崔溥回国后,在朝鲜受到的磨难的文章。[33]这篇文章首先收录在葛振家主编的《崔溥〈漂海录〉研究》中,之后又以韩文翻译后登载。另外,尹致富在建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韩国海洋文学研究》中,将《漂海录》放入海洋文学的记事类进行了分析。[34]以后尹致富把目光转向了19世纪的韩文谚解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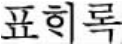 (漂海录)》,并以现代韩国语重新翻译,添上了简单的注释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35]
(漂海录)》,并以现代韩国语重新翻译,添上了简单的注释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35]
4.《漂海录》特集和探访集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有崔溥《漂海录》特辑,或者连载探访崔溥的中国旅程的纪行文,大大提高了一般大众对崔溥和《漂海录》的关心。其实,在更早的1973年,在现在已经停刊的《读书新闻》上,权五惇以《韩国海洋文学的白眉——漂海录》为题,把内容进行压缩后分12次进行连载。[36]从连载的第一篇中,登载的郑炳昱的简略的解说来看,这次《漂海录》的连载中,似乎郑炳昱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韩国海洋文学的白眉”这一题目和前面提到的张德顺的文章题目一样,但郑炳昱在《读书新闻》连载之前的1961年开始,以张汉喆《漂海录》为对象,他已经开始准备文章的委婉的说法。[37]这次连载事实上虽然只是《漂海录》的比较粗糙的节选翻译,但是它让一般大众第一次知道了《漂海录》的存在。
进入90年代后,先是韩松周在《光州日报》以《湖南学——崔溥》为题分5次连载。这篇文章虽然以崔溥这一人物为中心,但是其中只有两回是对《漂海录》的记述而已[38],之后在《韩国日报》,崔珍焕分2次连载了《沿着锦南先生〈漂海录〉》,这篇比较短的纪行记是参加了崔基弘、葛振家组织的探访队后发表的,它仅记载了宁波、苏州、杭州、北京等一部分崔溥经过的地方。[39]同一年,金井昊以长篇连载形式在《无等日报》连载了特别企划的《沿着漂海录》,分19次登载。[40]虽然经过了长期登载,使用了太多的版面,但和《漂海录》相关的部分变得较少,从结果来看,给人一种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纪行的感觉。
另外1997年明知大学探访队用了两周时间探访了《漂海录》里的中国旅程。这个探访队去了被推测为崔溥漂流的登陆地,浙江省三门县的海边,由此开始,经桃渚、宁波、绍兴、杭州、扬州、淮安、高邮、徐州、天津、北京、山海关、北宁(广宁)、辽阳进行了非常充实的探访,朴泰根以《崔溥的明朝漂流记——漂海录》为题,将其探访记分14次连载在《韩国日报》。[41]参加了这次探访的笔者的探访记《沿着崔溥的足迹》虽然当时没有发表,但2003年在季刊《展开明天的历史》中分3期连载。
5.最近的《漂海录》研究
最近的《漂海录》研究趋势中,最突出的是以曺永禄为首的东国大学的几名研究者。曺永禄在1995年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崔溥〈漂海录〉所描写的十五世纪下半期中国—朝鲜士人官僚之批判性观察》为题,进行了口头发表之后,[42]以此为起始,东京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主管的“东亚(朝鲜、中国、日本)近世社会的比较研究”研究项目的论文《对近世东亚三国传统社会比较史的考察——崔溥〈漂海录〉和日译〈唐土行程记〉为中心》开始出现扩散。[43]这篇论文通过比较《漂海录》和日译的《唐土行程记》,将研究焦点对准了中国、朝鲜、日本的异质性深化的东亚三国的社会变化。另外,在《漂海录》中,崔溥对中国进行了批判,在《唐土行程记》中,清田君锦通过“考”对朝鲜进行了批判,这一点也形成了对比。之后发表的《15世纪韩、中两国的文化异质性——以崔溥的〈漂海录〉为中心》,是将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内容要点,以韩国语改成了论文。[44]这篇论文虽然具有通过南方航路记述了浙东地区的韩中交流的特点,但是从整体而言,无论是研究目的或研究方法来讲,和前面的论文非常相似。受到曺永禄影响的徐仁范和朱圣志在《曺永禄教授定年记念论丛》上登载的论文中,各自将崔溥看到的江南都市、风俗、人物和崔溥一行乘坐的船舶和漂流航路进行了研究和分析。[45]徐仁范又对崔溥看到的江北和辽东,进行了记述。[46]
同时,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也影印和刊行了《燕行录全集》,其中包括了《锦南漂海录》。[47]《锦南漂海录》也是旧态依然地以藏书阁本为底本,在对于其他版本的调查比较粗糙的情况下,又选择了藏书阁本,不知道其中的理由。自1962年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刊行的《燕行录选集》中包含了《漂海录》以来,将近四十年后,又将《燕行录全集》影印刊行,但是对于连“解题”都没有附上,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当然与《燕行录选集》上下册包含30种燕行录相比,从份量上达到100卷的《燕行录全集》包含了380余种《燕行录》,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其收集的辛劳。但是,这仅是单纯的收集和影印而已,不仅连《燕行录选集》中的“解题”都没有,而且连最基本的简单说明也缺失。为了纪念《燕行录全集》的出版,以“《燕行录》和东亚细亚研究”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也热热闹闹地举行了。[48]这和同一时期,京都大学的夫马进编纂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的充实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9]2003年,在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的燕行录解题小组的主持下,《燕行录解题》一、二卷出版刊行,但这不是已经出版的《燕行录全集》380余种的解题,而是未收集本《燕行录》100余种的解题而已。[50]
崔溥一行漂流到中国的登陆点为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牛头门一带的海边。但是2002年7月,在离这里有些距离的宁海县越溪村树立了“崔溥漂流事迹碑”,这里是为了把崔溥一行移送杭州,在桃渚所接受调查的地方,其实是崔溥一行出发两天后,到达的越溪巡检司所在的村庄。这座纪念碑是崔氏宗族和浙江省宁海县政府合作,用了8年时间才树碑,为了揭幕式也算是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座谈会。而且11月韩国光州湖南大学和中国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结下了姐妹校际关系,以此为纪念,以“崔溥的《漂海录》为契机观察的韩中交流增进方案”为主题在光州湖南大学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曺永禄的基调演说“锦南《漂海录》的东亚交流史研究和几种课题”对其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性压缩。在主题发表中,刘俊和的“崔溥和《漂海录》具有的意义”内容非常疏略;金基周的“关于《漂海录》的作者崔溥的研究》”,不仅对研究史的整理有些错误,还有不少遗漏。[51]这次国际会议,与其说是把目标放在纯粹的学术性研究,不如说是为了宣传崔溥,对研究的期待,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合常规。
过了好久,日本学者松浦章在《明代漂到中国的朝鲜船》为题的论文中,局部性地就崔溥的漂海问题进行了讨论,开始表明了对崔溥《漂海录》的关心。[52]另外,以京都大学的夫马进为代表的研究小组以“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际秩序と交流の历史研究”为主题,开始了共同研究,在2003年2月22日召开的第2次研究会中,中国南京大学范金民以“朝鲜人の眼から见た中国の运河风景——崔溥《漂海录》を中心として”为题进行了发表。这意味着,在中国现在出现了以明清史研究者进行的崔溥《漂海录》研究已经正式开始。
范金民在2004年3月出版的《人文知の新たな总合に向けて》中,对《漂海录》评论到:
可以说,有关运河市井风貌的看法,在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上,崔溥的《漂海录》不但时代最早,而且在明代的同类记载中也唯一的。崔溥的看法,不独清晰形象地揭示了明中期特别是十五世纪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关于运河沿岸的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城镇风情等珍贵资料,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53]
曺永禄在2005年发表的《1488年的明和朝鲜——〈漂海录〉和〈朝鲜赋〉的相互认识》,是把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从另一种角度进行整理的文章[54]。朴元熇也把之前积攒的崔溥《漂海录》的研究成果,在2005年一一发表,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将漂流民的送还程序和情报传达、弘治中兴的征兆、15世纪中国人的朝鲜认识进行考察后,以3篇论文和对崔溥《漂海录》的7种翻译本的评论,作为那一段时间的成果。[55]
回顾五六十年代的Meskill、牧田谛亮、高柄翊开始的崔溥《漂海录》研究,在最近我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研究者的外延大为扩张,研究的幅度也大为增加。以后的课题研究中,就算是研究者的数量为少数也没有关系,我认为以15世纪东亚史为专业的研究者,对崔溥《漂海录》的研究,将从最初崭新的视角研究转为进行精密的研究。因此作为这样的精密研究的结果,我们期待着,崔溥《漂海录》在15世纪东亚史研究中,成为可以利用的国际性朝鲜史料而占有一定的地位。
【注释】
[1]这一书名是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在1962年出版《燕行录选集》下卷时,为将崔溥的《漂海录》和其它《漂海录》进行区别,把崔溥的号标在前面,又叫《锦南漂海录》。将《漂海录》以《锦南(崔溥)漂海录》为题收录,作为由来之始端。之后,高柄翊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成宗朝崔溥的漂流和漂海录》序言中,谈到“《锦南漂海录》这一名称之下,留下的漂流记……”,之后这一书名就如此确定下来。崔溥另有一本叫《锦南集》的文集存世,日后肃宗二年(1676)后世子孙将《漂海录》与《锦南集》合编一册刊行于世。因此将《锦南集》和《漂海录》联系起来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了和其他各类的《漂海录》区别,如有张汉喆《漂海录》或者文淳得《漂海录》,将崔溥的号放到前面,叫《锦南漂海录》。
[2]John Meskill,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P’yohae-rok(漂海录),“Acknowledgement”1958,Meskill教授在最近的采访中承认,“对崔溥的研究,大约始于1950年代的韩国战争时期。当时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了京都大学的宫崎市定教授,了解到明代时,朝鲜官吏崔溥曾经在中国六个月期间,以日记形式留下了丰富的见闻和观察,这就是崔溥的《漂海录》。以后,Meskill将《漂海录》译为英文,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深深地被《漂海录》描述的深奥的作品世界吸引”。《月刊中央》,2004年11月号。
[3]牧田谛亮,《漂海录》,《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下)》,法藏馆,1959年。
[4]牧田谛亮,《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记》,《金泽文库研究》第272号,1984年。
[5]John Meskill,Ch’oe Pu’s Diary: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Tucson,1965.
[6]高柄翊,《Meskil〈锦南漂海录〉译注》,《东洋史学研究》1辑,1966年;《崔溥的漂流记》,《东亚史的传统》,一潮阁,1976年再收录。
[7]郑炳昱,《漂海录解题》,《人文科学》6辑,1961年;《对漂海录》,《对韩国古典的再认识》,弘盛社,1979年再收录。
[8]《燕行录选集》,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年。(www.chuimin.cn)
[9]高柄翊,《成宗朝崔溥的漂流和漂海录》,《李相伯博士回甲纪念论丛》,1964年;《崔溥的锦南漂海录》,《东亚交涉史之研究》,首尔大学校出版部,1970年再收录。
[10]金炳夏,《从崔溥和哈梅尔的漂流记中看到的社会面貌和意识构造》,《文化批评》5卷1号,1973年。
[11]金炳夏,《对崔溥〈漂海录〉的研究》,《漂海录》,庆熙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1978年。
[12]金灿顺,《漂海录》,《纪行文集(1)》,《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9》,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1964年。
[13]金灿顺,《漂海录》,《纪行文集(1)》,《朝鲜古典文学选集20》,文艺出版社,1988年。
[14]许文燮,《漂海记》,《纪行文集》,图书出版海努里,1994年。
[15]洪林(编),《漂海录》,《纪行文集》,《朝鲜古典文学选集(19)》,1991年。
[16]李载浩,《漂海录》,《国译燕行录选集》,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年。
[17]崔基弘,《漂海录》,三和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崔周容,《漂海录》,极东精版社,1984年。
[18]崔基弘,《锦南先生漂海录》,教养社,1989年;崔溥《漂海录》,教养社,1997年。
[19]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国语国文学事典》,新丘文化社,1981年。
[20]崔康贤,《韩国海洋文学研究》《,省谷论丛》12辑,1981年;《纪行歌辞的类型的考察》,《韩国纪行文学研究》,一志社,1982年再收录。
[21]牧田谛亮,《漂海录と唐土行程记》,《金泽文库研究》第272号,1984年;《唐土行程记谈义》,《神田博士追悼中国学论丛》,1986年。
[22]金在先,《崔溥〈漂海录〉与明代海防》,《圆光史学》第4辑,1986年;《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集》,1987年再收录。
[23]金在先,《明弘治年间南北水陆交通及卫所之考察》,《第四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集》,1991年;《明弘治年间中国江南江北的人文社会生活及习俗之考察》,《第五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集》,1991年;《〈漂海录〉中明弘治年间之苏州景观》,《第九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集》,1994年;《崔溥〈漂海录〉与明代弘治年间之杭州地区景观》,中国社会史学会第五届年会及“地区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1994年;《崔溥从明国还国后经历考》,《第十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集》,1995年。
[24]张德顺,《海洋文学之白眉〈漂海录〉》,《旅行和体验的文学——国土纪行》,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87年;《纪行、日记的白眉〈漂海录〉》,《韩国随笔文学史》,图书出版博而精,1995年再收录。
[25]高柄翊,“崔溥”;崔康贤,“漂海录”;李东述,“锦南集”,《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1991年。
[26]崔溥人名中的“溥”应该读为“bu”还是“bo”,就这一问题浙江大学陈辉和笔者之间在网上有过一些讨论。参看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都市论坛:陈辉,《韩国学研究的危机——从两个人名的误读说起》,http://club.zj.com/429425/spacelist-blog-page-2.htm1;往复论坛,朴元熇,《读陈辉〈韩国学研究的危机——从两个人名的误读说起〉》,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lf2c296e55979127c7c75538blef4c05& threadid= 26877.
[27]葛振家,《漂海录——中国行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28]崔来沃,《漂海录研究》,《比较民俗学》10辑,1993年。
[29]葛振家主编,《崔溥〈漂海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30]《光明日报》199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1995年6月27日,《东亚日报》1995年7月11日。《当代韩国》秋季号,1995年9月。
[31]葛振家,《〈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讨》,第二次朝鲜研究环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1994年;《崔溥〈漂海录〉价值再探析》,第三次朝鲜研究环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
[32]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
[33]杨万鼎,《锦南崔溥〈漂海录〉撰进中带来的磨难和戊午士祸的考察》,《全罗文化研究》第8、9辑,1997年。
[34]尹致富,《燕行录选集所载崔溥的漂海录》,《韩国海洋文学研究》,学文社,1994年。
[35]尹致富,《注解〈 漂海录〉》,图书出版博而精,1998年。
漂海录〉》,图书出版博而精,1998年。
[36]权五惇,《漂海录》,《读书新闻》(12回)1973年5月20日—8月12日。
[37]郑炳昱,《漂海录解题》,《人文科学》6辑,1961年。
[38]韩松周,《湖南学——崔溥》,《光州日报》1993年5月15日—6月19日。
[39]崔珍焕,《追踪锦南先生〈漂海录〉》,《韩国日报》(2回)1994年6月18日—7月7日。
[40]金井昊《,沿着漂海录》《,无等日报》(19回)1994年11月1日—1995年4月4日。
[41]朴泰根,《崔溥的明朝漂流记——漂海录》,《韩国日报》1997年9月1日—12月22日。
[42]曺永禄,《崔溥〈漂海录〉所描写的十五世纪下半期中国—朝鲜士人官僚之批判性观察》,《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年。
[43]曺永禄,《对近世东亚三国传统社会比较史的考察——崔溥〈漂海录〉和日译〈唐土行程记〉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64辑,1998年;《近世东亚三国的国际交流和文化》,知识产业社,2002年再收录。
[44]曺永禄,《15世纪韩、中两国的文化异质性——以崔溥的〈漂海录〉为中心》,《近世东亚三国的国际交流和文化》,知识产业社,2002年。
[45]徐仁范,《在朝鲜官人眼中闪现的中国的江南——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朱圣志《,通过漂海录的韩中航路分析》《,东国史学曺永禄教授定年记念论丛》,2002年。
[46]徐仁范,《崔溥〈漂海录〉研究——崔溥描写的中国的江北和辽东》,《国史馆论丛》102辑,2003年。
[47]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锦南漂海录》,《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48]第21届韩国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燕行录》和东亚细亚研究”,东国大学韩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12月7日。
[49]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2001年。笔者还没有得到这本本应该被广泛利用的书籍,仅是根据夫马进介绍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东洋史研究》第61卷第4号,2003)的文章,大概了解了一下,除此之外没有办法。
[50]韩国文学研究所,《国学古典燕行录解题》,儒城文化社,2003年。
[51]国际学术会议“以崔溥的《漂海录》为契机观察的韩中交流增进方案”,光州湖南大学湖南发展研究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2002年11月21日。
[52]松浦章,《明代漂到中国的朝鲜船》,《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乐学书局,2002年。
[53]范金民,《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崔溥〈漂海录〉为中心》,《人文知の新たな总合に向けて》第二回报告书“历史篇”,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编,2004年。
[54]曺永禄,《1488年的明和朝鲜——〈漂海录〉和〈朝鲜赋〉的相互认识》,《东亚细亚历史中的中国和韩国》,崔韶子教授停年纪念论丛刊行委员会,2005年。
[55]朴元熇,《明代朝鲜漂流民的送还程序和情报传达——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明清史研究》24辑,2005年;《朝鲜人看到的明弘治中兴的征兆——以弘治元年(1488)的崔溥〈漂海录〉为中心》,《中国学论丛》16辑,2005年;《15世纪中国人的朝鲜认识——以崔溥〈漂海录〉为向导》,《15~19世纪中国人的朝鲜认识》,高句丽研究财团研究丛书9,2005年;《崔溥〈漂海录〉翻译述评》,《韩国史学报》21号,2005年。
有关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的文章

2章崔溥《漂海录》校勘记引言1. 6种版本的对校2.对校结果的分析3.对中国文献的校勘小结引言在朝鲜时代,崔溥《漂海录》在壬辰倭乱之前和之后,各出版3次。崔溥《漂海录》有6种版本之多,非常有必要通过对校,对文字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调查。1964年,在金灿顺第一次节译了崔溥《漂海录》。笔者先对崔溥《漂海录》的6种版本,进行了对校,想在决定研究所需底本时,留下确实的根据。......
2023-11-30

[4]李载浩,《漂海录》,《国译燕行录选集》,(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古典国译丛书,1976年。[6]崔周容,《漂海录》,(首尔)极东精版社,1984年。[8]葛振家主编,《崔溥漂海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朴元熇,《崔溥漂海录研究》,(首尔)高丽大学校出版部,2006年。[13]朴元熇,《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2023-11-30

但是崔溥《漂海录》中,除了以上的3种版本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版本。为了崔溥《漂海录》的完美的译注,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开展研究,对版本的调查必须先期进行,这一重要性是必须重复的。而且,通过这一过程选择最为适合的版本,作为译注的底本,这也是笔者为了开拓研究,对崔溥《漂海录》版本不得不亲力亲为进行考察的重要原因。......
2023-11-30

《唐土行程记》在初版26年后,改名《通俗漂海录》再次出版。最新出版的韩文翻译本是2004年出版的徐仁范、朱圣志的《漂海录》。另外,牧田谛亮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译注工作,但是以阳明文库本的《漂海录》......
2023-11-30

探访游记:沿着崔溥的足迹1.韩国人为什么不知道崔溥?在漫天灰尘中,奔驰的汽车内,忍受着颠簸,在脑子中却是装满了,寻找朝鲜时代历史人物崔溥足迹的想法。与死亡进行了13天殊死搏斗之后,最终崔溥一行乘坐的海船漂流到中国浙江省的某个海岸。在杭州接受了最终调查的崔溥,为了返回朝鲜,通过大运河被移送到北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之后,出人意料地受到明朝皇帝的赏赐。......
2023-11-30

由于《通俗漂海录》和《(漂海录)》是把崔溥《漂海录》原文压缩后进行的翻译,所以难以和原书保持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翻译上的错误仍然非常明显。日本的《通俗漂海录》,相当于朝鲜的所谓“坊刻本”。......
2023-11-30

十五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日记体著作,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富有学术价值。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运河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又完整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之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因而弥足珍贵,颇具价值。崔溥在杭州待了七天,经由坝子桥入京杭大运河回朝鲜。......
2023-10-31

3章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以崔溥《漂海录》为路标引言1.对朝鲜文化的理解2.对朝鲜历史的认识3.对朝鲜人物的关心小结引言为了考察明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我们广泛查阅了同时代的中国和朝鲜文献。因此,明代中期记录的崔溥《漂海录》,虽然不能视为典型的《燕行录》,但是它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在15世纪的有关大运河旅程的记录中,崔溥《漂海录》的准确性和详细程度,当然是首屈一指的。......
2023-11-30
相关推荐